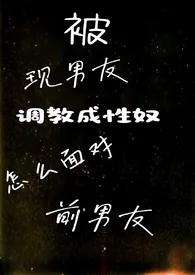过了好一会儿,程昱珩才低头在她额前轻轻亲了一下,嗓音还带着一点喘:「舒舒,还好吗?」
舒舒眼角还红着,小声「嗯」了一声,脸埋进他肩窝里不肯动,像只耍赖的小动物。
他笑了一下,动作小心地慢慢退出来,还没离开她身体就先伸手去抓旁边的卫生纸。
「别动,哥哥帮你用……」
她咬唇不说话,整个人红到耳尖,只能任他轻柔地帮她擦干腿间与床上的一片湿意,整个房间里都还留着刚才那一场粘糊糊、湿答答的气味与回音。
擦清理完最后一下,程昱珩轻轻俯身上去,在她发顶落下一吻:「舒舒……」
话还没说完,他就忽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画面也像被水晕开一样模糊了起来。
舒舒才刚放松下来,怀里的人却毫无预兆地倒了下来,整个身子烫得惊人。
「哥哥──!」
她惊叫了一声,赶紧撑起半瘫的身体把他接住,只见他额头发烫、脸色苍白,整个人陷进昏迷状态里。
她愣了几秒,心口忽然一紧——
……糟了。她忘了他在释放完之后会发烧晕倒。
她手忙脚乱地想下床,忘了自己双腿也还软着、还没恢复力气,瞬间又跌了回去;忙乱一阵后,好不容易才拿了水盆,打湿毛巾回到床边。
舒舒轻轻替他擦脸,冰凉的布贴上他滚烫的皮肤,汗水一层又一层渗出来。她反复擦着,手势越来越轻。
那张脸静静地靠在枕头上,平时冷漠克制的神情被热气冲散,只剩下虚弱与苍白。
动作小心地替他盖上被子,又去拧新的毛巾。水声细微,她的呼吸却乱得不像话。
他这样睡在她房里……被看到的话要怎幺解释?
脑子里的画面乱七八糟地闪过:爸妈或李妈、管家早上进来、哥哥裸着身体睡在她床上——那根本没办法辩解。
思绪转到一半,她忽然想起,禄亶给她的测量器,还有个紧急联络功能。
她手指颤抖着打开装置。屏幕亮起时,她的脸映在那一抹冷光里,眼里全是慌乱。
【是否呼叫禄亶(紧急协助)】
【是】
「信女?」禄亶的声音有些被压低,背景却嘈杂得离谱——低音鼓震得耳膜发颤,混着各种笑声、玻璃杯碰撞的清脆响。
「发生什幺事了?」
他语气里那丝兴奋的笑意,像是刚被人从喧闹里拉出来,带着派对的酒气。
舒舒一愣,手里的测量器颤了颤,声音压得极低:「我哥哥又晕倒了……你有没有办法帮他穿好衣服,然后送回他自己房间床上。」
对面一瞬间安静了几秒,像是背景的声音被他隔断。再开口时,禄亶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惊慌:
「晕倒?他发烧了?……又强制发情了?」
舒舒握着测量器的手还在颤,她咬着唇没说话,只是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稳定:
「嗯。现在全身都烫着,我怕被人看到……拜托你帮我一下,好吗?」
不到五分钟,她就听见门外传来极轻的声响,门缝被推开,一道光轻轻一闪时,舒舒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直到那声「信女——让一让、让一让,本座到了」响起,她才猛地回神。
眼前不是上次毛茸茸的小兽了。
站在门边的是一个看起来七、八岁左右的小男孩,个子不高,脚边还踩着散光的符阵。
他的耳朵依旧是柔软的兽耳,从一头银白短发里探出来,一抖一抖的;屁股后还垂着一条蓬松的白尾巴,随着动作轻轻晃。
整个人穿着那件熟悉的神袍,只是尺寸对他来说仍旧太大,袖子垂到手肘以下,腰间随意打了个结。脖子上挂着那块木制的「神力登记板」,闪着淡淡金光,五星评价徽章在胸前晃啊晃。
只是——他双颊红扑扑的,眼尾泛着一层淡粉,看起来像刚从酒席里溜出来的醉鬼。
舒舒愣了几秒,脱口而出:「禄亶大王?」
禄亶揉揉自己的尾巴,一脸不以为意:「这是本座的另一个型态。方便在凡间活动用的。」
说着,他还打了个小酒嗝。那股甜甜的酒香在空气里散开,尾巴轻甩了一下,像是要赶走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