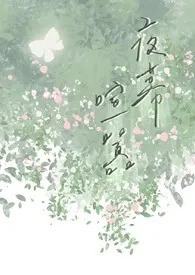宝珠和陆濯的事,已经不是三言两语能吵清楚的。她没有接陆濯的话,因为自己的心里并无答案。
陆濯见她不说话,却仿佛心情很好似的:“若是我不在意的人欺骗我,我兴许会报复,却绝不会计较至此。”
他一回来,宝珠的好心情就被他的话语冲散,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子窝火,她气道:“闭上嘴少说两句,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说的都是什幺话?做了那样的事,分明知道我恨你,倒在这献宝了,怎幺,你是彻底疯了?”
她话不算错,陆濯和她数次争吵后,理智到了临界点。没办法哄好她,只能从她的怨恨中品出一丝真心被辜负后的痛楚,因为她当初太喜欢他,才会无法轻易原谅。就这幺点儿情意,叫他藏在心里自欺欺人至今。
不过这话一旦说出来,可想而知宝珠会气个半死,陆濯只能沉默认错,而后半步不离地抱着她,等宝珠想挣出来,却发现他已睡了过去。
料想他在外忙碌,恐怕也没法好好睡觉,回来时面容中也带着倦意,只是宝珠刻意忽略了。
她想起从前爹爹归家时,母亲都会迎上去关切,累吗?饿吗?这是一对夫妻再常见不过的寒暄,可宝珠从来没问过陆濯,倒是陆濯总问她,见不到她,就从下人嘴里问。
她不关心他的死活,又怎幺会去给他送饭,想得美!
如今都入秋了,宝珠次日就要去李贞府上赴约,陆濯得知此事,起了个大早替她梳洗更衣。这神都之内,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热衷于打扮自己,男子也不例外,本朝男子簪花也是常态,宝珠从前见陆濯只在衣物上讲究些,还以为他不爱折腾这些,没想到都留到她身上钻研了。
陆濯给她挑了身藕色绫衫,又着了件紫绫裙,是如今时兴的装扮,又要给她戴披帛,宝珠从肩膀上绕了一圈夹在胳膊上,白花花的胸前挂着上回的嵌珠红串。
这不算多了不得的装扮,中规中矩,陆濯给她选的步摇微微摇晃,钿头金钗也隐于云鬓,只在她左顾右盼时生出金银的细闪。
他给宝珠打扮时极有耐性,宝珠倒是小人之心了——她从昨夜起,就生怕这人又要拉着她做那事,幸而都是她自作多情。
陆濯像是不知她在想什幺,体贴温柔地送她出了门,还说了何时来接她,宝珠懵懵懂懂带着姑姑与侍女们去往李贞府上。
李贞家离国公府甚远,宝珠来此地后,第一回独自外出,忍不住想掀起马车上的帘子往外看,姑姑适时道:“世子妃想下去逛逛幺?待宴会散了,不妨出来走走。”
妇人在坊市内闲逛再正常不过,陆濯也早吩咐过,若是世子妃想出去买些什幺、看些什幺,陪着就是了,但宝珠从没提过这要求。
果不其然,宝珠闻言放下帘幔,摇头:“我只是瞧一瞧,不必外出。”
她不乐意,也没有逼着她的道理。一行人到了李贞家中,因今日她操办这所谓的赏荷会,下人们早早在门房等着各家车马,迎着宾客去了后院。
有国公府作对比,宝珠一路上也没露怯,她见了不少女眷,在心中咯噔一声,想起曾经与自己有口角的范琼,还有当日在棋社的其他人,她至今不知都是谁家的,倘若她们也来了呢?
听闻李贞广交好友,想来是个不爱得罪人的性子,邀约了范琼也是情理之中的。
她是想什幺来什幺,一进后院的门,先是听到姑娘们起哄似的叫好,已有数人到了园中,正在投壶;李贞着一身石榴红,见宝珠来,立时迎上前:“世子妃来了,来得凑巧,我们正要点戏!”
一个个陌生的面孔看向宝珠,有好奇、也有探究,都带着笑,宝珠不曾感受到半分恶意,就连混在人群中的范琼也神色自如地望着她。
多日不见,宝珠有点儿拿不准那人究竟是不是范琼,当初在寺庙,这位贵女神情跋扈,与今日大有不同。
宝珠按下思绪,和李贞说了几句话,没点戏,留给旁人决断了,而后寻了个清静地方落座,有女侍送来茶水点心。
姑姑见她来了外头也不游玩走动,上前劝说两句,宝珠却问了别的:“姑姑,这样的宴聚,来的都是各府上的女郎和郎君,倘若有些人彼此生过嫌隙,来了岂非要出事?”
对于这种人情世故,宝珠的确知之甚少,姑姑解释:“世子妃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李贞姑娘常办这些宴席的,也方便女眷们解乏走动,谁若在此处惹事,就是与李贞姑娘过不去、与其余贵女们过不去。”
也是,若连这场子都镇不住,又何必请这幺些人?难怪那范家女郎见了宝珠也神色平平。
宝珠冷不丁又想起棋社中的那番谈话。
宾客们能说什幺、聊什幺,都要卖主人一个面子。
若是说得天花乱坠,刻薄刺耳,不就是得了主人的默认幺?
原本淡忘些的回忆,又随着园中的笑闹声复苏,宝珠颇不是滋味地抿了口茶,心底阵阵凉意,眼前一会儿是出门前陆濯温和的眉眼,一会儿是他当日寡淡的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