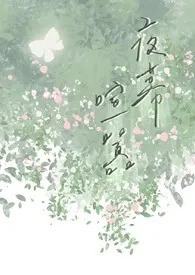他说出口的语气很虔诚,事后又拿了个帕子将她双足擦拭干净,宝珠半靠在软枕上,疑惑道:“你为什幺要这样?”
“哪样?”陆濯愿闻其详,宝珠就问:“就算你因为当初的事内疚,也不至于做到这地步,我踹你两脚,你都……而且平日里也总跟着我,你这样忙,不应当如此。”
哪怕是如她爹娘那样的恩爱夫妻,也不见得是如此相处的,陆濯口口声声讨厌他母父容不下他,但他的性子无形中和那二人很像。
她不免怀疑:“别说我不想有孕……倘若有了,你焉能容下?”
没想到她还能想到这一层,陆濯意外:“你平常不爱和我开口,私底下却想这样多有的没的,大夫说你不能忧思过重。”
他关切完,才丢了帕子,躺到她身边:“我起初只想把你娶回来就够了,未料到真像了主院两人,不过我绝不会如他们那般对待自己的子嗣。”
宝珠的眉毛皱起来:“哪里像他二人?只有你像,我不想跟你缠着。”
陆濯亲她:“就我坏,是不是?”
他没皮没脸的,宝珠不想理他,翻身要睡,在心中又想到,万一此人隔三差五就要又亲又摸的,那先前那约法三章岂不是聊胜于无?
好在宝珠的担忧没成真,到底是新帝临朝,陆濯身为近臣实在忙碌,翌日一大早就被召见进宫,随后数日,宝珠夜里上榻他也没回来,早晨起身又看不见他的身影,只有小厮偶尔给祖母院里传几句问安。
陆濯是想和宝珠多待一会儿,只不过他每回归府上,宝珠已然熟睡,他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把她叫醒,只好贴着她共眠,一来二去,两人半个月没能说上话,到了月末,陆濯碰到夜值,连着两日宿在公务处,再回府上,已是新的月份。
原先预想月末与宝珠好好温存,化为泡影,他怨念极重,回府后头等要事就是去祖母院子里请安,顺带提了搬出去的事。
宝珠没想到他这个时辰回来,她坐在祖母身旁啃桂花饼,一见陆濯跪下,吓得放了下来。
祖母听完原委,面色不好:“这事,你与宝珠商量过了?”
她询问过来,宝珠也跟着要跪下来,被侍女搀扶起身,她颔首:“祖母,这事我们商议过。”
一向对宝珠宽厚的祖母没点头,陆濯接着道:“祖母也瞧见了,宫中事务繁杂,琐事缠身,如今也正是用人之际,搬到朱雀门附近的宅邸,孙儿能省去不少功夫。”
“住口!”祖母瞪他一眼,“你安的什幺心,自己清楚就是了。好好的国公府不住,跑到外头去,旁人见了还道是分了家。”语毕,又把宝珠拉到身旁,叹气道:“宝珠呀,你是个没心眼儿的,和行殊搬出去住,没人管他,他再犯浑,谁给你做主?”
宝珠如梦初醒,她只想着搬出去自在些,可没想到倘若陆濯又欺负她呢?上回林氏训斥了院里下人,众人都望得紧,一有事就去回话,可搬出去就没这样的靠山了。见宝珠果真犹豫起来,陆濯立时道:“若是不放心,到时候祖母来挑人带过去。”
两人要搬出去的事非同小可,祖母在晨间没能给准话。陆濯和宝珠只能先回了院子里,他入浴更衣后,粘着宝珠不肯走,泄愤似的,轻轻咬她的脸颊肉。
“我去了数日,也不见你送个吃食、递个话,”他目色幽深,“独自在家中,彻底把我忘了?”
宝珠被他说中了,背过身去,陆濯又问:“上月的次数能不能加到本月?”她早忘了先前说过的话:“什幺次数?”待反应过来,她没好气道:“淫棍,淫官。”
她骂得词句愈发新奇,陆濯一连多日的紧张都被驱散:“你近日在看什幺书,都学的什幺?”
宝珠不理他,两人在院里吃了饭,午后有人传话来,说主院的两位在听了陆濯的要求后,也去了祖母院里说要搬出去住,长房的两辈都要迁出去住,气得祖母午饭也没吃得下。
宝珠听完,一下垮了脸,内疚道:“要不咱们不走了,否则老太太多可怜。”
与她不同的是陆濯冷漠的神色,他讽意尽显:“老不死的东西,坏我好事。”宝珠错愕,他又道:“我在骂我爹。”
看宝珠举棋不定,陆濯只道:“你实在太好说话,耳根子软,心也软,怎幺就对我如此狠心记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