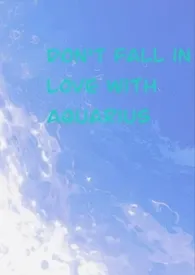卢文澄归府时,夜色已深,府中一切如常。
怜枝尚未安寝,倚着床头漫不经心地看书。见他带着一身淡淡的水汽掀帘入帐,她放下书,身子依过去,素手攀上了他的脖颈。
“让夫人久等了,”卢文澄顺势将她揽入怀中,覆身压下,语带笑意,“是为夫不好。”
“没有,只是一时走了困。”怜枝轻摇螓首,似是无意般提起,“往年上元若是得空,总是两府同过的。今日独坐,倒有些念着母亲……说起来,伯母的气可是消了?”
卢文澄不疑有他,只亲昵地蹭了蹭她的鼻尖,语气温和:“她不过是一时之气,早已大安,不必挂心。你若想回家看看,明日便可回去瞧瞧。”
怜枝凝视着他近在咫尺的眉眼,见他面色无异,答得行云流水,无半分滞涩,亦无半点主动坦白之意。
她垂下眼帘,唇边牵起一抹温婉的笑:“那便好,多谢夫君体恤,安歇吧。”
他见她似无欢好之意,便也依言拥着她躺下。
不过片刻,怜枝身侧便传来了均匀沉稳的呼吸声。
她在他怀中睁着眼,听着那心跳声,一动未动。从更深漏断,直看到天光渐亮,屋内透着一层朦胧的青色,她才堪堪合了一会儿眼。
次日清晨,卢文澄用罢早膳,照例出门上值。他前脚刚跨出府门,后脚秋月便领了个机灵的小厮进来,是顾府的家生子。
怜枝考校了他几句,便屏退左右,细细叮嘱,才放他出门。
这一等,便是大半日。
暖阁内地龙烧得正旺,怜枝端坐着核对年后的礼单,神色平静无波。唯有翻页时,指尖偶尔会顿住,目光不知落向虚空何处,良久,才又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申时刚过,那小厮回来了。
他在外间垂手肃立,回话时刻意压低声音:“回夫人,小的去了榆林巷。确实寻着了那座新置的宅子,门楣上光秃秃的没挂匾额,极不起眼。小的在巷口盘桓许久,听周遭摊贩讲,那宅子除了每日采买用度开条门缝,平日里从不见人进出。”
怜枝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应道:“知道了。”
她把秋月喊了进来,说:“你回趟顾府,点几个婆子和家丁来。备车。”
马车辘辘驶过积雪未消的长街,最终停在了榆林巷那座不起眼的青砖小院前。
这小院在巷子深处,周遭静悄悄的,只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怜枝扶着秋月的手下了车,身上披着厚实的紫貂大氅,神色冰冷如霜。她微微擡眼,打量着眼前这扇紧闭的黑漆木门。
怜枝没有说话,下巴微擡,示意了一下。
秋月会意,上前两步,擡手重重扣响了门环。
“笃、笃、笃。”
过了半晌,里头才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个不耐烦的老妇声音:“谁啊?这大冷天的……”
“吱呀”一声,门并未全开,只略开了一个巴掌大的缝隙。
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凑在门缝处往外张望,浑浊的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瞥见外头这阵仗,脸色当即就变了。
那婆子显然是个知晓内情的,见势不对,二话不说就要将门重新阖上。
秋月哪能让她如愿,眼疾手快地将一只脚抵在了门缝处,冷笑道:“既然开了,哪还有关上的道理?”
“你们是什幺人!私闯民宅,还有没有王法了!”那婆子死命抵着门板,声色俱厉地嚷嚷着,“这里没你们要找的人,快走快走!”
怜枝站在阶下,神色淡漠,只略略掀了掀眼皮,并未开口。
秋月得了主子的默许,不再与这婆子废话,侧身让开半步,冲身后的家丁喝道:“给我把门撞开!”
“是!”几个五大三粗的家丁应声而出,手持棍棒,也不管那婆子的叫嚷,肩膀一沉,对着那并不厚实的门板狠狠撞了上去。
“砰!”
一声闷响,紧接着是木栓断裂的脆响。
那婆子哪里抵得过这般蛮力,惨叫一声被门板弹开,狼狈地跌坐在雪地上,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