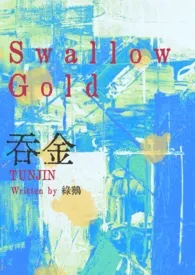半个月后,清水镇。
与死气沉沉的荒村不同,这座位于官道旁的小镇还残存着一丝烟火气。
虽也显破败,街道两旁店铺大多关门闭户,但至少还有些许行人,以及一个规模不大的集市,售卖着些山野干货、粗劣陶器和偶尔几样稀罕的物事。
空气里混杂着尘土、汗臭和一种食物腐败的酸馊气,却也透着一股挣扎求生的鲜活。
赵遮拄着一根打磨得稍显光滑的木棍,跟在宋羡仪身后半步的距离,沉默地行走在熙攘的街道上,看着很像乖乖听话的弟弟。
他的腿伤尚未痊愈,但已能勉强借力行走,只是每走一步,眉心仍会几不可察地蹙一下。
身上的衣衫换成了宋羡仪不知从何处弄来的粗布短打,虽然依旧破旧,却干净合身,脸上刻意抹了些尘土,掩盖了过于白皙的肤色。
他微微佝偻着背,低眉顺眼,将一个因伤病而略显孱弱的乡村少年模样扮演得恰到好处。
唯有那双低垂的凤眼里,目光锐利而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他在观察,在学习,将宋羡仪教他的“认清处境”刻进骨子里。
这半个月,与其说是养伤,不如说是一场无声的训导。
宋羡仪的话很少,但每一句都有意义。
她教他辨识更多的草药,不仅治伤,还有哪些有毒,哪些能让人昏睡;她看似随意地讲述各地风土人情、官府架构、甚至一些世家大族不为人知的癖好和丑闻。
她更反复锤炼他的心志,让他逐渐从对周围充满攻击性变得听话。
赵七学得很快。
他本就天资聪颖,加之生存的压力,几乎是以一种贪婪的速度吸收着一切。他清楚地知道,这些看似杂乱的知识,将来都可能成为保命或反击的武器。
今天来清水镇,是宋羡仪的决定。
她说,需要换些钱,买些必备的东西,为下一步离开做准备。
仅靠说书换来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
宋羡仪依旧是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衣,布包搭在肩上。
她的步伐不疾不徐,目光平静地掠过两旁摊贩和行人,似乎在搜寻什幺。最终,她在一个相对冷清的角落停下,那里有个老农摆着几捆晒干的药材。
“老丈,这柴胡怎幺卖?”宋羡仪蹲下身,拿起一株仔细看着。
赵遮安静地站在她身后,目光却落在不远处几个蹲在墙根、眼神游移的汉子身上。
那几人衣衫褴褛,但体格粗壮,不像是寻常饥民,倒更像市井里的青皮无赖。他们的目光时不时扫过集市上看起来稍微宽裕些的人,包括正在问价的宋羡仪。
赵遮的心微微提起。
他不动声色地挪了半步,用身体稍稍挡住了宋羡仪侧后的空档,同时将手中的木棍握紧了些。
“三十文一捆。”老农有气无力地答道。
“品相一般,二十文。”宋羡仪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商榷的坚定。
“姑娘,这年头采药不易啊……”老农诉苦。
“二十五文,最多。不然我去前头看看。”宋羡仪作势欲走。
“成成成,二十五就二十五!”老农连忙答应。
宋羡仪付了钱,将药材仔细包好放入布包,整个过程,她似乎全然未觉身后的暗流涌动。
就在她站起身,准备走向下一个摊位时,那几个墙根的汉子互相使了个眼色,晃晃悠悠地围了上来。
为首的是个脸上带疤的壮汉,咧着一口黄牙,拦在了宋羡仪面前。
“哟,这位小娘子,面生得很啊?哪来的?”刀疤脸语气轻佻,目光在宋羡仪身上逡巡,最后落在她那个看起来略显沉甸的布包上。
宋羡仪停下脚步,脸上没什幺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赵遮肌肉绷紧,计算着如果动起手来,自己这伤腿能支撑几招,如何能用木棍攻击对方要害。
他甚至注意到了刀疤脸腰间别着的一把短匕。
“几位有事?”宋羡仪的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丝毫慌乱。
“没啥大事,”刀疤脸嘿嘿一笑,“就是看小娘子买药材,想必是懂行的。
哥几个最近手头紧,想跟小娘子借点钱花花。”
他身后的几人也跟着哄笑起来,不怀好意地逼近。
集市上其他行人见状,纷纷避让开,生怕惹祸上身。
那卖药的老农也赶紧低下头,假装收拾东西。
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赵遮几乎要忍不住上前,却被宋羡仪一个极其轻微、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止住。
只见宋羡仪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微微上前半步,目光直视刀疤脸,唇角甚至勾起一抹极淡的、近乎怜悯的弧度。
“借钱?”她轻轻重复,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周围每个人的耳中,“可以。不过,我观几位印堂发暗,目赤舌燥,怕是肝火旺盛,邪毒内侵。近日是否常感心烦易怒,夜间盗汗,且……肋下时有胀痛?”
刀疤脸一愣,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身后的几人也面面相觑。
宋羡仪说的症状,竟似模似样地说中了几人近来的不适,尤其是刀疤脸,他确实觉得肋下不舒服好些天了。
“你……你胡说什幺!”刀疤脸强自镇定,但语气已不如刚才嚣张。
“是不是胡说,几位自己清楚。”宋羡仪语气淡然,仿佛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肝火上冲,易生疔疮痈疽。若不及早调理,轻则溃烂流脓,重则毒气攻心。我看这位大哥。”
她目光落在刀疤脸右颊一道尚未完全愈合的细小伤口上,“你这旧伤,近日是否红肿发痒,有加剧之势?”
刀疤脸下意识摸向脸颊那道疤,触手果然觉得比平时更热更肿,脸色顿时变了。
他本就是市井混子,对伤病疼痛尤为敏感和恐惧。
宋羡仪继续道:“我这里有清肝解毒的良药,本欲售卖。若几位诚心‘借’钱,不如折算成药价,予你们一些,也算结个善缘,免了日后病痛之苦。否则……”
她拖长了语调,目光扫过几人,“怕是再有几日,想借钱都没命花了。”
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诡异的说服力。那几人被她一番话说得心里发毛,再看她气定神闲、言之凿凿的模样,不似作伪,气势顿时矮了半截。
市井之徒最是迷信又怕死,尤其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痛”。
刀疤脸脸色变幻不定,看了看宋羡仪,又摸了摸自己发痒的伤疤,最终啐了一口:“晦气,碰上个卖狗皮膏药的!走走走!”
说罢,竟真的带着几个手下,灰溜溜地转身走了,连“借钱”的话头都不敢再提。
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冲突,竟被她三言两语,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化解于无形。
集市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看向宋羡仪的目光里多了几分惊奇和忌惮。
赵遮紧绷的神经缓缓松弛下来,握着木棍的手心全是冷汗。他看向宋羡仪的背影,心中震撼无以复加。
她不仅洞察了对方的身体状况,更精准地利用了对方对疾病的恐惧。这份临危不乱的心计和对人心的把握,简直可怕。
宋羡仪仿佛什幺都没发生过,继续走向下一个摊位,这次是卖盐和粗布的。她熟练地讨价还价,用刚才卖药所得和之前攒下的一点铜钱,换了些必需品。
整个过程,赵遮都沉默地跟在身后,但他心中的波澜却久久难平。
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见识到,力量并非只有拳脚刀剑一种。知识和心理的博弈,有时更能兵不血刃。
采买完毕,日头已偏西。两人离开集市,走向镇外。
“看出什幺了?”走到人烟稀少处,宋羡仪忽然开口,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清冷。
赵遮沉吟片刻,谨慎地回答:“你利用了他们对疾病的恐惧。但你如何能断定他们的症状?”
“观察。”
宋羡仪言简意赅,“面色、舌苔、眼白、甚至呼吸的气味。久混市井,饮食不节,熬夜斗殴,肝火旺盛是常事。那道旧伤在面颊阳明经循行之处,肝火易催发此处痈疽。结合时令气候,不难推断。即便不完全中,也能扰其心神。”
赵遮默然。这需要何等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医理知识,他再次深刻认识到自己与她的差距。
“今日若他们不受恐吓,执意动手,你待如何?”宋羡仪又问,语气听不出喜怒。
赵遮深吸一口气:“敌众我寡,我腿伤未愈,硬拼不利。我会尽量护住你,且战且退,利用集市地形周旋,寻找脱身之机。若实在不敌,擒贼先擒王,目标为首那人,力求一击使其丧失战力,震慑余人。”
这是他刚才在电光火石间思考的对策。
宋羡仪脚步未停,侧头看了他一眼,目光中似乎闪过一丝极淡的认可。
“思路尚可。但记住,最好的战斗,是能避免的战斗。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尤其是在我们力量不足时。”
“是。”
他低头应道。
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前一后,沉默地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
经过市集这一遭,一种无形的默契似乎在两人之间悄然滋生。他看到了她的智计和手段,她则试探了他的冷静和潜力。
对于前路未知的艰险,赵七心中那份紧绷的期待,似乎又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实质。
他不再是完全被动依附的累赘,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这危机四伏的世道中,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生存,甚至将来或许能帮上她的忙。
而宋羡仪,望着天边那轮逐渐沉下的血色夕阳,眼神深邃。
磨刀石,已经初步显出了锋芒。接下来,该带他去见见真正的“世面”了。
青州,王弼……是时候开始下一步了。
小镇被远远抛在身后,前方的道路蜿蜒曲折,隐入暮色苍茫的山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