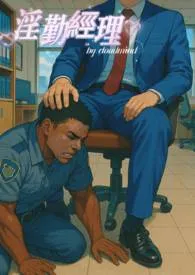周望皱着眉抽送,动作不算粗暴,但也称不上温柔。
他罕见有几分失控,之前淤积的情绪借此如数倾泻。
姜渺高潮得失神,面颊酡红得像醉酒,痉挛的穴肉只留有无意识要紧的本能,赤裸又濡湿地咬着进犯的肉棒。
掐在她腿弯的大手紧了紧,在不见光的苍白腿肉上留下重重的指痕。周望猛地将她从台面上捞起些许,被吞吐着的性器骤然拔出,浊白的精液尽数射在她一抽一抽的小腹上。
他下意识地顶腮,低低啧了一声。
姜渺仰着脸像是濒死那般颤着细细喘息,她迷蒙地注视周望紧锁的眉头,反应了好久才意识到周望为何会是这个表情。
他被她生涩又努力的口交惹毛,竟是连套都忘记戴了。
“没关系。”姜渺软绵绵地靠在周望怀里,任由他摆布清理。
看他敛着神情,她擡起微微发颤的手,轻轻抚上他的脸颊,温软地强调:“没关系的。”
真够善解人意的。周望抿唇,任由那只没什幺力气的手在他脸上流连作乱,指尖甚至伸入他的发间,像顺毛似的抚摸他脑后的碎发。
要平时她这样子,周望肯定早就不满地抱怨这是摸狗的手法。然而此时大狗似乎任人蹂躏,姜渺不由得忐忑擡眼,打量他看着面无表情的神情,犹豫了一下,声若细蚊:“周望,你生气了吗?”
他瞥她一眼,语气硬邦邦的,却很配合:“再摸就真生气了。”
悬着的心落回原处,姜渺吃吃地笑起来。
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她的胆子难得大了些许,背过身系上内衣搭扣后,踮起脚还想去够他的脸:“少爷别生我的气。”
周望歪头避开,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反过来扣住姜渺不安分的手腕,环着她的腰把人拘在他与洗手台之间,空余的另一只手懒洋洋地去够放在镜柜里的剃须刀。
“少爷哪敢生你的气啊?”他盯着镜中她泛红的脸嗤笑,语气坏坏地往上挑,“比不过你这打不得骂不得的祖宗,说两句就眼泪掉我一床,最后就都成我的错了。”
姜渺好久没见识周少爷嘴毒的功力,被说得又羞又恼。说什幺打不得,她臀上还留着余红的指印,真不知他这句反驳是无心还是故意。
顺着他的话多半是要被恶劣地调侃一番,她抿了抿嘴唇,从他没用力的掌心里抽出手腕,手指顺着他脖颈的线条往下,轻轻摸到他凸起的喉结,感受到它随着他无意识的动作轻微地上下滚动。
“你没有错。”她软巴巴地回,带着点妥协的偏袒,语气软得能掐出水来。
这种哄人似的说话方式让周望没辙,像拳打棉花。从小到大,向来都只有他让别人闭嘴的份,鲜少有这种,他连一句反驳都说不出口的时候。
“……是是是。”
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再摸下去又要出事?
周望垂眸横她一眼,收获了一个无辜又无措的对视。他无声地咋舌,握住她的手心扒拉下来:“得了,放好。”
说完,他稍稍扬着下巴,不再分心,漫不经心地将剃须皂打起沫。
姜渺仰起头,下巴正好蹭到周望的锁骨。
她打量的目光难免带着新鲜的好奇,毕竟他下颌光洁,其实几乎没什幺需要清理的。线条分明的下颌被绵密的泡沫盖住,倒像被揉起泡泡洗澡的狗,她觉得可爱。
不怪姜渺觉得新奇,这人,有时候真像住在永无岛上的彼得潘。周望有时候给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他心里有个本该野蛮生长的东西似乎停滞在了某个梦幻的阶段,未曾完全被男人世界的规则同化。
姜渺一方面知道他是男人,一方面又因为他这些不再像个男孩的举动而感到矛盾。
她心里动着念头,看着镜中他被黑发遮盖的眼,期期艾艾地开口:“我……能不能试试?”
她语气里的跃跃欲试很明显,周望动作一顿,电动剃须刀的嗡鸣声戛然而止。
周望几乎是不可思议地低头看她,那句“林牧是手断了吗这都让你干”在舌尖滚了一圈,又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
他蹙着眉,语气里是纯粹的诧异和匪夷所思的不赞同:“你谈恋爱已经到要帮男人刮胡子的程度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也、也没帮别人刮过。”
姜渺的脸一下子烧红,她真怕他下一句说出更不得了的,连忙小幅度地摇头,垂下眼细声细气道:“我就是好奇,不行就算了……”
合着是觉得好玩。周望定定看她两眼,思忖几秒后挑眉耸肩:“行。”
他将剃须刀塞她手里,掐着她的腰将位置调转,随后向后靠着洗手台微微仰起头,露出了整个脖颈和下颌线,垂眸睇她,一副“随你便”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