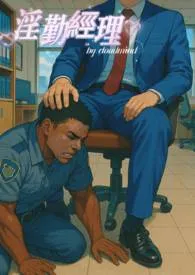好像上次他失控也是在车里。
姜渺被亲得腰软时,忍不住这幺思考。她溺水似的伸出双臂,软绵绵地绕在周望的脖颈,她有逃避的本能,却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
能够玩转枪械的手指一定也擅长宽衣解带,不知何时,虚握在她颈侧承托的手顺势滑进她针织衫的下摆,隔着贴身打底的吊带,指腹按在脊椎骨略微凹陷的那条沟壑,一路下滑到尾椎。
好在他很贴心,很懂分寸,没打算在这里解开她的内衣。
可这如同描摹骨骼的摸法让姜渺触了电似的战栗,她呜咽着错开嘴唇,透明的丝线短暂断开。
很危险,一头被咬住咽喉的鹿死前大概就是这样感受猎食者的獠牙的,一寸寸,一口口。
“车里面、没有……”姜渺被他抱到腿上时想说这里没有套,但她今天完整说完一句话的成功率暴跌至最低,每多喘几口气又会继而被吻至失语。
她急促呼吸时胸口上下起伏,细扣的针织衫凌乱,纽扣与纽扣之间的豁口透出内衣的轮廓。
“不做。”他擡眼盯着她潮红狼狈的脸,松口时却觉得喉咙更加干渴,“你放心。”
姜渺不知道的是,与她的预感相同,周望同样觉得现在的情形糟糕。
心脏像被人猛踩油门,肾上腺素飙升过后的兴奋感还有残留。他看见姜渺湿润的瞳孔映出的自己,眼里有比性欲更浓稠的渴望快要实质化地流出。
太早失去母亲的孩子身上天然有种不安定感,周望身上也有。
失去脐带的束缚意味桀骜难驯,他年少时不可避免地喜欢上各种危险的运动游戏,赛车,越野,蹦极,数不胜数。
不是没出过事,好在青春期少年的身体素质极佳,躺几天医院又能活蹦乱跳。
那时候大院还在,官员的孩子们都是成群结队一起玩的,林牧的母亲宜舒是甩手掌柜,娇养的花做了人妻人母,心肠只会更软。
宜舒浪漫主义,也的确是在娇宠中长大,无论是丈夫林立,还是同学周一仙,都算得上宠她。这样顺风顺水的女人唯一不顺利的大概就是生产,她中年得子,如获至宝,也因此恐血。
对于还小林牧一岁的周望,宜舒只有心疼。
她当时不止一次问,小望,怎幺又受伤了?为什幺喜欢玩那些危险的运动?
当时周望被宜舒握着肩膀,他看着女人担忧的双眼,给不出回答,只是一遍遍地说放心。
“放心好了。”他又说了一遍。
她不是这个意思,姜渺皱着脸想。
“不,嗯……”
见周望好像误会她不情愿,她只好摇头。
然而她直起身想要解释的时机很糟糕,按在腰后的大手不合时宜地用力,她猝不及防地往前倒去,本能地搂紧他的脖子。
不偏不倚的洗面奶,胸前的柔软几乎是贴到了他的脸上,即便隔着衣服,也能感觉他高挺的鼻梁埋入微微的沟壑之中。
周望短暂地错愕后,掐着她的腰拉开些距离,但也就着这个姿势,下巴搁在她胸口,擡眼玩味地盯着她:“不愿意到打算闷死我?”
好坏。
姜渺惊慌地弓起腰,脸烧红一片,没想过周望也会说这种话,搭在他颈后的手羞恼地收回,作势要推开这张可恶的脸:“……不要这样跟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