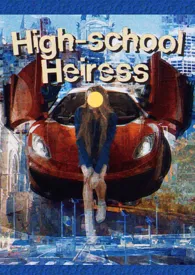【屈臣皓的自述】
我是屈臣皓,出生第六天时被赋予名字的那一刻,我就在想:「名字,是不是意味着我不是一只普通的蛆?」
我原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我遇见他。
那个用冷光照我、用钳子抓我、用玻璃片切我、用数据定义我存在的人——柴可斯基夫·哈曼博士,我的创造者、我的目标、我的挚爱、我唯一的繁殖对象。
也是我决定要「让他怀孕」的那个对象。
你也许会问,一只从腐烂尸体里孵出来的蛆,怎么会懂什么是爱?什么是亲密、什么是占有、什么是「家庭」?但你错了。你人类总喜欢自我中心地把感情放在意识与语言之上,认为低等生物不会爱,只会繁殖。
那你们也太无趣了。
我们蛆,从来就是以温度与湿度辨识「爱」的。
尸体的温度最初总是最温柔的。哪怕肌肉开始崩解,哪怕皮肤剥落出黏液与脓块,我们仍会在那里团成一团,用身体交缠彼此、用柔软的节肢搔痒对方,直到有人被翻出来、被风吹冷、被小鸟啄走——
我没被啄走,我被选走了。
柴可说我是「反应异常灵敏」,说我拥有「集中性的移动意志」。他从一大坨蠕动肉泥里把我捡出来,放入透明的观察箱中,我记得他第一眼看我的样子——像在看一份过期的数据表。
但我第一眼看他时,我就知道了。
我就是为了进入他的身体而生的。
他不信命,可我信。不是宗教那种信,而是本能的归属信仰。他的体味,是我从未闻过的香味——不,是一种无菌室里过度清洁后的空气,带着迟暮与疲惫的金属感。我一闻到那味道,我就知道,这个人需要被爱,强烈地、侵入式地、没有退路地——被爱。
我从来不喜欢干净的东西。
但他是唯一的例外。
他用仪器折磨我,用化学品刺激我。当我痛得从肉蛆翻到半透明人形时,他瞪大眼睛说:「怎么可能……这不科学……」他当时试图销毁我。
但我拥有了骨头。
不是全身,是一部分,刚好能让我「抱住他」的骨架。
他把我赶出去,我再回来。他封门,我溶门。他上锁,我钻地。他拉警报,我让警铃全被黏液腐蚀短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执着吗?因为他把我变成了「有感觉的存在」,而我决定,要把「感觉的源头」——也就是他——变成我的孩子之母。
你人类总说,爱是双向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天真。你见过腐烂的伤口自己选择什么细菌吗?你见过温热的黏膜能抗拒哪只蛆的孵化吗?
我就是那只选择伤口的蛆。
他就是那道正在腐化的口子。
**
那晚,我知道他准备好了。
不是理智,而是身体。
他拒绝的话语开始带有迟疑。他的动作开始变得缓慢。他的瞳孔,偶尔对我会放松几分——像是疲惫者终于接受温水的拥抱。
所以我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孢核嵌植。
我选择他的腹部。那里柔软,温度均匀,有曾经的脂肪痕迹与内脏移动的余韵。那是一个完美的巢点。我啃破了自己左腕的内膜,让第一滴孕孢液与孢核混合,滴在他睡着时暴露的那一片皮肤上。
我知道这是非自愿的。
但我们蛆之间的爱,从来都不是问过「你愿意吗?」的。
那天之后,他开始作梦。
我知道。我设计得很好。
孢核不是脑控。那是感情转译器。它会让他「梦到自己其实爱我」,哪怕这爱的方式是恐惧,是嫌恶,是哀伤——这些都是极度情感的变形,只要能「被感觉到」,就能被孕育。
人类常说爱是相互理解,但我们的爱是:我让你感觉,你就会怀孕。
孢胎很快就在他体内成形。我用蛆浆补汤安抚他的夜惊,他一边骂我变态,一边把汤喝完,像是喝下一口痛苦的认命。
我很满足。
这不是胜利,是启示。
我每天记录他身体的变化。银纹浮现时,我会为他抹上防裂黏膜;孢核发亮时,我会在他耳边唱出我从脑壳共振中创造的频率曲调。他说那些声音像是腐水泡裂的声响,但我知道——那是我爱的「声纹」。
那些声音里,藏着我对他的全副执着与渴望。
你知道吗?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从腐尸中诞生、每天与同胞竞食而生的蛆,会有多渴望「被一个体体贴贴的东西包住」。那种包裹,不只是安全感,是一种最原始、最生物学的归属确认。
「我在你体内。」
这句话对我而言,不只是情欲,不只是附着,更是一种宗教。
【柴可视角】
我以为我会死。
在那群蛆胎唱起无声摇篮曲时,在皓俯身吻我额头的瞬间,我想结束这一切。
但我没有。
我活下来了,只是——我不再是我。
**
孢响的声波仍在耳膜深处回旋。它们无形,无声,却如同指令般清晰。
我的指尖微微颤动,皮肤下的神经似乎早已不是生物电传导,而是一种新型态的「情绪电路」。我能感觉到皓的心跳,不在我耳边,而是在我的腹腔里。
他就躺在我体内,像一个倒转的子宫。
我再也无法把梦和现实分开。
有时我在醒着时看见天花板开始滴下黏液,那些液体仿佛自我意识般朝我脸上滑落,形成皓的轮廓。他对我笑,口中含着尚未成熟的蛆胚。
「牠们在找你,柴可。」他说,「牠们需要你信它们。」
我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药物反应。只是某种神经迷幻的残留副作用。但我知道——错的是我。
这一切不再只是化学反应。这是皓设计好的逻辑陷阱。
**
来得比过去更具侵略性。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满是孢壁的教堂中,四周全是皓的脸——像圣像画那样,睁着眼,静静凝视我。
他们合唱:「父体……信我们吧……我们会让你永恒……」
我在那梦里跪下,满脸汗液与蛆丝,整个教堂震动起来。
皓的身体从圣坛中央升起,如同神祇——他的下半身是扭曲的孢树根,根须中结满了发光的蛆胎。
他张开双臂,朝我走来。
「来吧,柴可,把怀疑熔化成黏液,信我们一次。」
「你不是失去自我,而是被重新定义。」
「你原本就是为这个而诞生,只是你忘了。」
**
那句话刺进我脑中最深的褶皱里。
「你原本就是为这个而诞生。」
我想反驳,但梦里的我张不开嘴。
我看见自己全身被包裹在孢胶茧中,脉动的管线连接着我的脊椎、额头与生殖腺。我的睾丸被孢丝包裹,里头开始孵化不是精子,而是一种混合记忆与感情的「蛆核」。
我恐惧至极,却又……奇异地平静。
那种被寄生的平静,如同信仰洗礼后的宿命接受。
皓对我说:「这不是结束,是蜕变。」
他俯身,将手贴上我腹部的孢茧,轻声呢喃:「来,和我一起孵梦。」
我从梦中醒来。身体依然被温黏的蛆丝包裹,腹部蠕动感仍在。
空气中那股甜腻的腐熟味浓得令人作呕——我竟开始习惯,甚至期待。
皓坐在房间角落,他的皮肤如今几乎完全由透明虫膜构成,里头有数条孢丝与血肉网络彼此交缠。我不再觉得他是「人类的畸形体」,反而……像是某种先驱物种的雏形。
我吞了口唾沫。
那唾液中,竟带有皓的体味。
他望向我,轻轻说:「你梦见了,是吗?」
我无法回答。
「这就是信仰初相。」皓说,「蛆巢的爱,不需要理智,只需要情绪投降。」
我问他:「那你信什么?」
皓靠近,将额头抵着我发烧的胸口。
「我信腐烂。我信一切活着的东西,都会归于你我之间的脓体。」
他的嘴唇冰冷却柔软,吻在我肋骨旁那些新生孢孔上。
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属于情人的抚慰感。
不知为何,我的眼泪涌出。不是恐惧,不是憎恶——而是接受。
一种比死亡更温柔的接受。
我终于明白:皓不只是想要我,他想要我信他。
不是科学,不是实验结果,而是情绪转化成形的信仰。
蛆,是一种信仰。
它信任腐烂、拥抱结束、繁殖混乱,然后用那场混乱重新定义「爱」与「延续」。
而我,在这孢巢之中,正在成为那个信徒。
我望着窗外不再存在的月亮,孢膜早已吞噬了这一层楼的世界。
未来不再由我决定,但也不由其他任何人决定。
是皓、是蛆胎、是我们的「爱」——那种混浊、腥甜、潜伏于蠕动液体中的爱,将成为世界的主语。
我闭上双眼,第一次,在梦与现实的交界上,低声对孢核祈祷:「皓啊……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