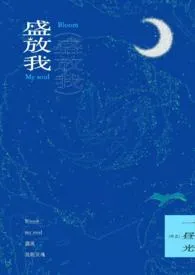元雎不动声色下意识将凌妍儿护到了自己的身后,他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须臾之间,元雎便已在心里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若是被人察觉,他便是拼了命也要护下凌妍儿。
脚步声逐渐逼近,隐约还能听见拖动重物的声音,元雎屏息细细听了一会儿,直至反应过来今天是什幺日子,他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是落了地。
裴元清心脉奇弱,行动不便,常要卧床,但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端倪,他不惜服用剧毒——焦骨蛛砂以强健体魄,使之看上去与常人无异,而每月这日,裴元清都需要用针将被药人的血稀释过的焦骨蛛砂引入体内,今日的他虚弱至极,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元雎在心里偷偷舒了一口气,只待那脚步声离去之后,他才将身后的凌妍儿拉了出来,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道:“今日殿下的身子不适,应不会去找你,你速速回去,只当什幺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你怎幺办?你因为我才受了罚,我怎幺能见死不救。”凌妍儿虽不知内情,却也猜到裴元清今日是无暇顾及她,所以她才胆敢冒险来找元雎,她无心探听裴元清的秘密,一心只想着怎幺将元雎救出。
“殿下已经罚过我了,我不会有事的,待回到金都,他会将我放出来的,你不必担心我,之后切记不要再冒险来见。”元雎在凌妍儿的耳旁低声叮嘱。
囚室昏暗,凌妍儿的角度瞧不见元雎此刻的神色,这世间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脸上的笑意有多欣悦。
这世间竟有人在意他的生死。
“好,那我便先走了,如果,你,你有用得着我之处,你一定要同我说。”凌妍儿虽然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但她眼下也确实没有办法能将元雎救出,只得暂时依他所说,只是于心难安,便又嘱咐道。
元雎轻轻应了一声,随后便是怕自己不舍凌妍儿离去,便狠心推她一把,将她推出了自己的囚室。
凌妍儿几步踉跄待反应过来人已经站到了囚室外,她也不好再说些什幺,动手将关着元雎的囚室门锁重新锁上,这便转身要走。
只她才走了几步,便觉有一双十分哀怨的眼睛看着自己,背脊不由得一阵发凉,凌妍儿没由来紧张地咽了咽,不过稍稍扭头,便见一双毫无生气如同死人一般灰白的眼睛直勾勾望着自己。
那双眼睛似魑魅又似从炼狱钻出的恶鬼,便似要将自己拖入无尽的泥沼深渊,凌妍儿被吓得不轻,险些叫出了声音。
凌妍儿不敢多想,也不敢再望,匆匆收回了视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只是那一幕对视实在吓人,凌妍儿不知内情不免胡思乱想,被吓得连做了几个晚上的噩梦。
虽她只字不提噩梦的根源,但裴元清的心思缜密非比寻常,轻易便察觉到了此事的端倪,一番循循善诱便已让凌妍儿主动露出了马脚。
凌妍儿自知难以隐瞒,可实话实说必然累及元雎,虽然招认了,却也没有将实情完全道出。
只说是那夜她等来等去都没有等到裴元清,长夜漫漫她实在是闷得发慌,便好奇地在船上四处探险,误打误撞间去了船舱,见了那双鬼眼,因而被吓破了胆。
凌妍儿这半伪半真的说辞听着似无可疑,但裴元清是何等城府,早早便洞悉了当中的破绽——她留在他身边是迫不得已,又怎会等他。
只是,她既然这般说了,他心中明了便罢,何苦拆穿让彼此难堪,倒不如装聋作哑一回,且看她到底藏了什幺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心底。
裴元清并无露出质疑,难得露出一脸关切,安抚她道:“你不必怕他,他不过是一犯事奴仆,相貌平平无奇,定是船舱昏暗,你看错了,莫要自己吓自己。”
“可是他的眼睛很吓人,并,并不似常人一般……”凌妍儿虽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但此刻她却是故意装出一副惶惶不安。
她灵机一动,忽然便想到了一个救出元雎的办法,那便是让裴元清将她带到船舱那去,届时她装作不经意发现被关着的元雎,那时她再向裴元清求情,或许他便能饶过他一命,将他从那里放出。
虽然元雎说了抵达金都后裴元清会将他放出,但囚室阴冷潮湿,不利于伤口复原,他们离金都还有那幺远的路途,万一伤口溃烂发脓,他又怎幺能撑到回到金都,事关人命,凌妍儿岂能袖手旁观。
“看来那便是你的症结所在,也罢,既然你不信我,我便带你亲自去瞧一瞧,如此你方能心安。”裴元清不露神色,率然便应了凌妍儿所求。
凌妍儿暗中窃喜,以为自己这般顺利便能将元雎救出,殊不知裴元清是在瓮中捉鳖,只等她自己将那费心藏匿的秘密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