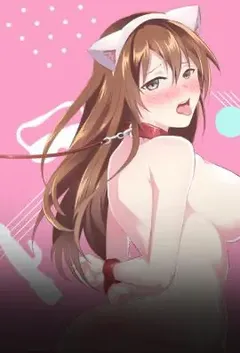第二日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昨晚一夜,混乱的梦境纠缠着我,让我睡得极不安稳。
我慌忙爬起来,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哑着嗓子问,“谁?”
“是我,开门。”门外传来筱月压低的声音。
我心头一紧,连忙披上外套,趿拉着拖鞋过去开门。
门一开,筱月闪身进来,手里还端着一个酒店常见的托盘,上面放着牛奶、煎蛋和几片面包,伪装成送早餐的样子。
但她的脸色却不像早餐那么温和,一对眼眸瞪着我,里面燃着压抑的怒火。
“李如彬!你们父子俩到底瞒着我干了什么好事!”她反手轻轻关上门,把托盘往桌上一顿,声音虽低,却字字带着火药味,“张杏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的‘按摩’又是怎么回事?老李他怎么敢对你的妹妹做那种下流事!”
我被她劈头盖脸的问话砸懵了,下意识地辩解,“筱月,你听我解释…是蛇夫,蛇夫他逼爸做的,他给了爸三天时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筱月眼中的怒火瞬间被一种冰冷的了然取代,她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哦?原来还有这么个‘选择题’?蛇夫定的?老李选的张杏?”
我这才反应过来,筱月刚才只是在诈我!而我这个从不说谎的老实人,在她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三两句话就漏了底。
看着筱月那混合着失望、愤怒和一丝受伤的眼神,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她面前,我本就没有任何秘密,也无需隐瞒。
我颓然地靠在墙上,将昨晚蛇夫如何如何下达那个变态的考验,以及我如何被迫向父亲传达,父亲又如何“选择”了张杏的经过,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筱月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紧抿的嘴唇和微微起伏的胸口显示出她内心的不平静。等我说完,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
就在这时,筱月耳尖的听见通廊外传来的脚步声和餐车滚轮的声音——真正的酒店侍应生来送早餐了。
筱月眼神一凛,迅速收敛了所有情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语速极快地说,“我去想想办法。你稳住,别露馅。”
说完,她不等我回应,便像一阵风般悄无声息地拉开房门,侧身闪了出去,离开了。
侍应生送来的早餐我食不知味,机械地吞咽着。刚吃完,房间里的座机就响了。
是蛇夫打来的,语气热情得过分,“李所长,起来了?今天天气不错,别急着回去上班了,难得我今天有空,务必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你这位‘知己’。”
我心中暗骂,嘴上却不得不敷衍,“蛇夫先生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
“诶,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蛇夫打断我,语气带着知己般的亲近,“就这样说定了,一会儿大堂见,带你去体验体验我们铂宫新开的项目。”
挂断电话,我只好给所里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正好是虞若逸,她声音清脆,“所长,您放心休息吧,所里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心里却丝毫轻松不起来。
来到大堂,蛇夫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一身休闲打扮,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我,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笑意。
张杏和筱月也在,张杏穿着运动装,气色看起来比昨晚好了不少。筱月则是一贯的沉静,挽着父亲李兼强的手臂。
蛇夫安排的“招待”极尽奢华。
先是去了酒店附属的保龄球馆。
这年头,保龄球还是项时髦运动,球馆里灯光锃亮,木质球道光滑如镜,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鞋油和抛光剂的气味。
蛇夫和张杏一组,我和筱月一组,父亲李兼强推说年纪大了不想玩。
蛇夫打球时动作优雅,成绩也不错,不时和身边的张杏低语几句,张杏则微笑着点头,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筱月运动神经很好,掷球动作干脆利落,成绩甚至超过了蛇夫。
轮到张杏时,她显得有些紧张,右手持球,助跑,挥臂,她的动作似乎仍然有些僵硬。
果然,在投了几球之后又一次出手的瞬间,她“哎呀”轻呼一声,右臂僵直的垂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怎么了杏儿?”蛇夫立刻上前关切地问。
“没…没事,”张杏蹙着眉,“可能刚才发力不对,右臂旧伤好像又拉到了…”她尝试着活动一下手臂,疼得吸了口凉气。
蛇夫随即对跟在旁边的父亲李兼强说:“李部长,看来又要麻烦你了。待会回去了带杏儿去水疗部那边,用你的手法帮她舒缓一下肌肉。”
父亲连忙点头,“应该的,蛇夫先生放心,交给我。”他先上前扶住张杏,帮她揉了几下止痛的穴位,态度专业而自然。
蛇夫又转向我和筱月,“李所长,小莺夫人,咱们别扫了兴,继续玩。”
打完保龄球,蛇夫又带我们去了酒店的私人小泳池。泳池区域装修得如同热带雨林,巨大的玻璃穹顶下,水温适宜。
换好泳衣出来,筱月穿着一件保守的连体泳衣,却依旧掩不住她挺拔的身姿和修长的双腿,引来不少目光。
张杏则是一件可爱的分体泳裙,她右手手臂拉伤,便不下水游泳了,只跟在蛇夫身边随便玩玩水,吃点水果。
蛇夫游泳技术还不错,飞鱼一样在水中穿梭。他游了几圈后,便靠在池边,和同样下水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话题从泳池的水质处理,莫名地拐到了“艺术”和“人性欲望”上。
“李所长,你看这水,”蛇夫掬起一捧水,看着它从指缝流走,“看似清澈,底下却藏着循环过滤的系统,还有各种化学药剂维持平衡。人的欲望也一样,表面可以装得道貌岸然,底下却汹涌澎湃。”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我,“有时候,直面欲望,甚至欣赏它,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和‘解脱’,你说呢?”
我明白他是在为晚上的“节目”做心理铺垫,我实在是难以苟同,却只能勉强挤出一丝赞同的笑容,“蛇夫先生见解独到,说得有道理。”
游完泳,已是下午。我们坐电梯下到酒店办公楼层,张杏如之前所说,跟着我的父亲李兼强去了铂宫酒店新开业的水疗馆。
蛇夫带着我和筱月去了他的办公室,处理所谓的“新项目资金文件”。其实就是一些账目核对和签字确认流程。
筱月业务熟练,很快将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蛇夫看着筱月高效的工作,眼中露出赞赏,但那份赞赏底下,总藏着一丝令人不安的审视。
资料整理完毕之后,还有几份关键文件需要父亲李兼强作为项目负责人签字。
筱月拿起文件,“蛇夫先生,李所长,那我下去水疗部找李部长签一下字。”
蛇夫点点头,还顺手拿多了一个鼓囊的文件袋给筱月,说,“顺便把这个也拿给李部长。”
筱月拿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
我和蛇夫继续讨论着棚户区“鱼陈邨”清理后的规划,蛇夫暗示后续可能需要警方“配合”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心不在焉地应着,心思早已飞到了楼下的水疗部。
父亲这次…应该不会再对张杏做什么了吧?
毕竟蛇夫没去偷窥,而且张杏只是手臂拉伤…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筱月还没回来。蛇夫交代的事情也差不多完了。我正准备起身告辞,突然——“啪!”的一声惊响。
办公室里的灯光瞬间全部熄灭,眼前一片漆黑,窗外透进来的光线显示,整个酒店的电力系统似乎都瘫痪了。
“怎么回事?”蛇夫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悦。
很快,走廊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酒店员工安抚客人的声音,“各位客人请不要惊慌,是总闸跳电了,我们的电工正在紧急维修,很快就能恢复供电!应急照明马上启动!”
片刻后,走廊和一些关键区域亮起了应急灯,勉强能视物。蛇夫嘟囔一句,“真是扫兴。李所长,我们出去看看。”
我跟着蛇夫走出办公室。
酒店里有些混乱,但员工训练有素,正在有序疏导客人。
我心系筱月,蛇夫跟工作人员要了一个手电筒递给我,说,“你妹妹和李部长还在水疗部那边,麻烦李所长过去看看。”
我点头说好,正好筱月刚刚也去了水疗部找父亲李兼强,我可以顺便过去看看。
水疗部在酒店的下一层,装修风格走的是低调奢华路线,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脚步声,墙壁是暖色调的软包,空气中弥漫着精油的芬芳。
此时水疗部也因为停电显得有些忙乱,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正打着应急手电,安抚着受惊的客人。
我借着昏暗的应急灯光线,一间间按摩房找过去。
大多数房间门都关闭着,隐约能听到里面按摩师安抚客人的声音,我试图仔细听,分辨出筱月或者父亲的声音有没有在水疗部的按摩间里。
一直走到水疗部最里面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我停在一个挂着“香薰理疗室”牌子的房间门外。
这里的隔音似乎更好些,但仔细听,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我俯耳过去倾听,其中一个声音,正是父亲李兼强!
我放缓呼吸,把脸贴近门缝。里面的对话模糊地传出来,似乎有一个女声,但声音被什么捂住了一样,含混不清。
父亲的声音带着神秘的诱导感,“别怕,放松点,用你的手,得用两只手…感受它…”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响起的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接着,那个模糊的女声响起,带着羞耻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战栗,“好…好粗…怎么好像…比刚才还要大…”
我僵在原地,手脚冰凉。断了电的黑暗中,我透过门缝隐隐望见一双纤白的小手,躺在按摩床上,怯生生地试着把一根巨大的棍状轮廓握住。
黑暗阻止我看清按摩床上女性的身材与容貌。
张杏…还是筱月?
我感到难以呼吸。
香薰理疗室内的声音断断续续,像细针一样扎着我的耳膜。父亲声音低沉的循循善诱着。
“对,就这样,从下往上捋,不用别紧张,轻轻地…” 父亲的声音带着粗重的呼吸,“我也来帮你…”
一阵细微的、仿佛衣物摩擦的窸窣声后,是那个女性一声极力压抑的惊喘,声音发颤,“…你怎么又碰那里…”
“哪里?”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动作似乎并未停止,“是这里吗?嗯?告诉我,感觉怎么样?”
细微的啧啧水声随着他的手指动作响起。
“…我不…不知道…” 女声仿佛在抗拒,又仿佛在无助地承受,“…你一弄…我变得好奇怪…”
“奇怪?是舒服的奇怪,还是难受的奇怪?” 父亲不依不饶,声音更近了,似乎贴在了对方耳边,手指上响动愈发迅疾,“快说实话…在我面前,不用装…”
那女子的娇喘愈发急促,呜咽着,破碎地吐出几个字,“…舒…是舒服…可是…”
“舒服就对了。”父亲打断她,语气带着肯定,伴随着一声似乎是手掌拍在肌肤上的轻微脆响,引得那女子又是一声短促的娇呼。
“你这身子,天生就是该被好好疼爱的…只是以前没遇见我这样的男人…瞧,只要我稍微碰一碰,就湿成这样了…”
门外的我听得面红耳赤,心中五味杂陈。
那女子的声音…虽然因为情动和压抑而变形,但仔细分辨,似乎……似乎并不完全像张杏?
难道里面不是张杏?
那会是谁?
是筱月吗?
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门内的对话还在继续。
“啊…你手上轻点…” 女子求饶着,声音带着一种被征服后的软糯,“…不能再…嗯…”
“不能什么?”父亲的声音带着笑意,动作似乎更加孟浪,“你看,你下面的小嘴咬我的手指咬得多紧…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东西…”
“…求你…停下…又要喷了…” 女子的哀求声越来越微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自控的、细碎的呻吟,仿佛防线正在崩溃。
一阵细微的、仿佛丝绸滑过肌肤的窸窣声后,是一个女子极力压抑的、带着痛楚的惊喘,声音发颤,似乎被什么堵住了嘴,又像是极力忍耐,“…呃!不可以…还是太…大了…你真是个疯子…”
女子的声音因为压抑和情动而变形,隔着门板更显模糊。我心脏狂跳,是张杏吗?还是筱月?
黑暗中,我无法分辨,只觉得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每一个音节都揪着我的心,更可耻的是,我的阴茎也在随着里面的情形勃起,变硬。
“别担心…”父亲声音体贴的说,“我不会伤害你…现在不会进去的…你看你流了那么水…我就在外面蹭一蹭…不会痛的…”
“…不…不行…”女子呜咽着,带着哭腔,床垫发出轻微晃动的声响,似乎是她在推拒父亲李兼强,“…你先拿出去一点…太满了…”
“现在可停不下来了…”父亲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伴随着一声更响更深沉的没入声,女子发出一声拉长音调的、被贯穿的悲鸣,随后化作了断断续续的、带着泣意的吸鼻声。
我的阴茎硬得发疼,父亲单单只是一个插入的动作,便已经令按摩床上的女子受不了。
父亲并没有立刻动作起来,而是在黑暗中,温柔地摩挲女子的肌肤,似乎在耐心的等候着她的小屄蜜肉适应他的硕大巨龙。
几分钟后,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放缓了许多,安抚着她,“好点了吗?是不是没那么疼了?”
女子没有立刻回答,只有调整呼吸的细微鼻音。过了好几秒,才传来一声极轻的羞涩回应,“…嗯…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
她的声音不再那么紧绷,虽然还带着颤音,但那股尖锐的痛楚似乎消褪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的、被填满后的无措。
父亲引导着她的小手,抚向她和自己的性器苟合处的外面,轻轻抚摸着。
“啊…”女子被吓了一跳,“你…你居然还没有一截没有…没有进来…”
门外偷听的我也听得暗暗心惊,心想父亲的在情事上的心思和功夫算得上“武林高手”了。
“我说了,我不会伤害你的。”父亲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得意,展现自己的虽然胯下有巨根,却不会粗暴地伤害床榻上的伴侣。
他说着,胯下和缓而有节奏动了起来,床垫规律响起的轻响,“感觉到了吗?我的阴茎在你里面脉动…你的身子,正在慢慢接纳它…”
“…别…别说这种话…”女子羞怯地抗议,但声音软绵绵的,反而像是在撒娇。
伴随着她的话语,是一阵细微的、肌肤摩擦绸缎的声响——我的眼睛适应黑暗之后,隐约看到女子脸上覆着绸缎。
这让我更加无法判断她的身份。
“好,不说。”父亲低笑一声,动作却并未停歇,那有节奏的声响逐渐变得顺畅起来,“那我们就…做点实在的…”
“…啊…你慢…慢点……”她声音变得黏腻起来,带着一种被抛入海浪里的恍惚 ,“…怎么会……这么深…你不准…不准再进来了…”
“都怪你流的淫水太多太滑…是你的小屄在欢迎我…”父亲的声音带着磁性,胯下的动作的力度和速度似乎在悄然加剧,床头因他的动作,轻轻撞击墙壁,发出规律的叩击声,“还不止…下面的小嘴还在缠着我的下面的大头…”
就在我听得心神激荡,几乎被门内那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吞噬之际,头顶的灯光猛地闪烁了几下,“啪”地一声,骤然亮起!
整个水疗部的通廊瞬间变得灯火通明,刺眼的光线让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几乎同时,我感觉到一只微凉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吓得浑身一颤,猛地回头——映入眼帘的正是我的妻子夏筱月!
她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身后,脸上带着一种似嗔似怪的表情,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看够了吗?听够了吗?”筱月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揶揄。
我心脏狂跳,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筱月在这里,那…那屋里那个脸上覆着绸缎、正在父亲身下承欢的女子,就绝不可能是她!
只能是张杏!
这个认知竟让我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然而,筱月她那只搭在我肩上的手,竟然顺势向下,迅速地探入了我的裤裆,隔着布料不轻不重地抓了一把。
“哼,果然硬得像铁一样。”筱月撤回手,瞪了我一眼,脸颊微微泛红,语气带着嗔怪,“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一个德行?跟那个蛇夫一样,就喜欢看这种活春宫?”
“不!筱月,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我急忙想否认,脸上烧得厉害,羞愧难当。
“行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筱月打断我,眼神警惕地扫视了一下恢复供电后逐渐有人走动的水疗部走廊,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说,“跟我来!”
她拉着我,快步走向隔壁一间同样挂着“香薰理疗室”牌子的房间,筱月用钥匙卡快速刷开门,将我拽了进去,随即反手锁上门。
房间里还残留着精油的淡香,布局与隔壁相似。
筱月没有开主灯,只打开了墙角一盏昏暗的壁灯。
她把我拉到房间内侧的一面墙边,那里有一个装饰性的、类似舷窗的圆形小窗口,窗口被一层薄薄的磨砂玻璃隔开,但透过玻璃,能清楚地看到隔壁房间的些许景象——正是父亲李兼强所在的那间香薰理疗室。
“这…”我惊愕地看着筱月。
筱月没有看我,而是从她随身携带的那个小巧的挎包里,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黑色的手持式摄像机。
“如彬,你听着,”她把摄像机塞到我手里,声音低沉而急促,“蛇夫不仅派我下来找老李签文件,临走时给我的文件袋里还装着这个。他在里面留了一张纸条,‘李所长一定会去偷窥李部长和杏儿的,到时候把这个手持摄像机交给他用。’”
我如同被一道惊雷劈中,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手中这台摄像机。我的行踪,竟然被蛇夫猜得一清二楚…
“他…他简直是个疯子!”我咬牙切齿的说。
“但他也是一个天才。不过,好消息是他现在完全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特殊癖好的人,获得了他的信任。”筱月叹了口气,眼神中充满了无奈,“这虽然很恶心。但如彬,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去击溃蛇夫。”
我握紧了手中的摄像机,冰冷的金属外壳刺痛着我的掌心。
我明白筱月的意思,这是卧底工作的一部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
但一想到要亲手记录下父亲和妹妹…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就在这时,筱月忽然蹲下了身子。在我惊愕的目光中,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开始解我的皮带扣,然后是西裤的纽扣和拉链。
“筱月!你…你这是做什么?”我下意识地想阻止她。
筱月抬起头,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眼眸中闪烁着水光,她带着妻子的歉意说,“如彬,作为你的妻子,我…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尽到妻子责任,所以…”
她低下头,动作有些笨拙但却异常坚定地将我早已勃起的阴茎解放了出来。“今晚…就让我来帮你吧。”
她声音温柔,“你拍你的,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我会帮你一起承担,就当是为了任务…也当是我补偿你的。”
说完,不等我回应,她便俯下了头,温软的双唇轻轻含住了我的龟头。
“呃!”我浑身猛地一僵,一股强烈的电流瞬间窜遍全身。
这种感觉,与在KTV厕所里和小薇那次完全不同。
这是我最爱的妻子,愧疚、感动、爱怜、以及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如同火山般在我体内爆发。
我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扶住了筱月的头,手指插入她柔顺的发丝间。
另一只手,则颤抖着举起了那台沉重的摄像机,对准了玻璃后,父亲李兼强房间里充满淫靡声响的景象。
父亲李兼强背对着我们这边,他强壮的身躯微微起伏,汗水沿着脊背的肌肉线条滑落。
张杏脸上覆着的黑色绸缎早已被汗水浸湿,紧贴着她脸庞轮廓,更添了几分神秘而脆弱的美感。
绸缎下发出的声音闷闷的,却更显得她此时的呜咽和呻吟是如此的身不由己和情动难抑。
“啊…慢…慢些…”
张杏的呻吟声破碎不堪,一双纤手无力地推拒着父亲宽阔的胸膛,指尖却在不自觉地蜷缩,仿佛欲拒还迎,“我不要…不要那么…深…”
父亲李兼强低笑一声,反而动作更加悍猛的挺胯,按摩床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他俯下身,臭嘴贴近张杏被绸缎覆盖的耳廓,声音带着一种可恶的戏谑,仿佛在讲授什么人生至理,
“受不住?傻丫头,这哪是受罪?你读书多,气血都淤在脑子里、心眼里,身子却僵得像块木头。我这是在给你活络经脉,排解郁结,待会儿就知道爽处了…”
他说着,腰胯猛地一沉,动作幅度大到令人咋舌。
“呃啊!”张杏猛地仰头,绸缎下的嘴张大了,发出一声近乎窒息般的尖叫,身体触电般剧烈颤抖起来,“骗人…你骗人…哪有这样…这样疏通的…啊呀!”
“怎么没有?”父亲喘着粗气,语气却愈发得意,带着一种混不吝的油滑,“老子这套‘李氏疏通大法’,专治你这种死读书、不开窍的闷骚小才女!瞧你这身子,嘴上说不要,里面又热又缠人,诚实地很呐!水儿流得哗哗的,难道不是爽得厉害吗?”
他的话语粗俗直白,像带着倒刺的鞭子,抽打在张杏残存的理智上,却又奇异地混合着一种令人面红耳赤的、无法否认的真实感。
“别…别说…羞死了…”张杏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似是哀求,又似是呻吟,双腿不由自主地盘上了父亲的腰,脚趾死死蜷缩,“才…才没有…嗯…嗯哼…”
“没有?”父亲似乎被她这口是心非的反应取悦了,动作变幻,没有尽根插入张杏小屄的硕长阴茎变成了九浅一深的节奏,不用几个回合就逼得她语不成调,“没有你夹这么紧?没有你叫床叫得这么动人?你们读书人就是嘴硬,老子这‘龙棒渡穴’,是不是直戳你的心肝?嗯?说,是不是?”
他一边说着混账话,一边精准地掌控着节奏,无须使出全力便能让茎身与龟头的每一次冲击直撞张杏灵肉最深处,让她理智崩坏,语无伦次。
“啊!…是…是…是那儿…别…别碰了…呜呜…我不要…妈妈…我不要…”她溃不成军,甚至在哭喊妈妈,身体像狂风中的柳条般摇曳,被动地承受着一波强过一波的猛烈浪潮。
“饶了你?这才到哪儿?”父亲似乎杀得兴起,大手隔着睡衣,揉捏着她的乳肉,言语更加不堪,“学问大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得让老子给你‘开光’,才能尝到这做女人的真滋味儿!你这身子,天生就是块宝地,欠耕!今天老子就给你深耕细作,种下点快活种子,让你以后都忘不了!”
“呜…混蛋…老流氓…嗯啊…轻…轻点啊…”张杏的骂声软糯无力,反而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她的身体彻底化为了欲望的载体,随着父亲的冲击而起伏呻吟,唾液已经沾满了脸上覆着的绸缎,小屄溢流的淫水也已湿透按摩床床单。
我和筱月在隔壁听着这淫声浪语,面红耳赤,心跳如鼓。
我手中的摄像机忠实地记录着一切,镜头因为我的颤抖而微微晃动。
筱月跪在我身前,用她的口舌的温柔的吮弄我的阴茎与龟头,抚平我那可耻的生理反应。
就在这时,父亲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房间里响起黏腻的啪啪肉击声响,张杏的叫床也陡然拔高,变得尖锐而连续。
“来了…来了啊!…受…受不住了…李…兼强…你这个…这个混蛋啊!!”
随着一声近乎撕裂般的哭喊,张杏的身体猛地反弓起来,僵直了足足好几秒,高潮时阴精淫液失控地喷泄着,直至父亲把未射精的硕长阴茎缓缓抽出,发出一声“啵”的轻响后,张杏才彻瘫软下去,只剩下剧烈而无意识的抽搐和呜咽。
父亲坐在她旁边安抚着她,一时间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在房间里。
摄像机冰冷的触感与筱月口腔的温热形成了强烈反差,看着父亲轻易在床上征服了张杏,以及阴茎被筱月的唇舌侍奉,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坚挺。
筱月的技术并不熟练,甚至偶尔会牙齿轻磕到我的龟头,但她极其耐心和温柔,努力适应着我的节奏。
她的鼻息喷在我的小腹,痒痒的,更添了几分撩拨。
她时不时会抬起眼看向我,眼神中充满了鼓励和爱意,仿佛在说,“没关系,我在这里。”
在这种复杂至极的感官和心理刺激下,我竟然坚持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的时间。
我的手稳稳地举着摄像机,记录着隔壁那场背德的戏码,而我的阴茎,却在妻子的口舌下,体验着一种扭曲的的快感。
“筱月…我…我要射了…”我喘息着,腰部微微颤抖。
筱月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她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深入地含入——这让我想起,在密室时筱月为父亲的巨龙口交时,那时,她含入父亲阴茎上的龟头时小嘴就被撑满了。
这时,筱月的喉咙发出轻微的呜咽声,好似在说,“我准备好了。”为父亲口交之后,她的小嘴能轻松容纳我那正常尺寸的阴茎。
我也在这最后关头,在筱月温暖的口腔中猛烈地释放了。积攒了数月的压力、焦虑、愧疚和爱意,在这一刻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射出。
筱月紧紧地含着我的阴茎,直到我完全平静下来,才缓缓抬起头。她的嘴角残留着一点白浊精液。
她脸颊绯红,眼眸扫过我阴茎依旧昂然挺立的窘态,又飞快地瞥了一眼那边已然瘫软如泥的张杏,鼻子里发出一声嗔怪和无奈地哼声,“哼…瞧你这样子!看着自己老爸…那样…居然能…这么精神…”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酸涩和羞恼,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又瞟向隔壁房间,仿佛被父亲李兼强那非凡的床事能力和强悍的征服力所震撼。
我顿时尴尬得无以复加,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阴茎塞回裤子里,结结巴巴地解释,“我…我不是…筱月,这是因为你…才…” 语言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要是躺隔壁按摩床上的人是我,你还会不会那么硬?”筱月羞着脸,问。
我愣了一下,着急忙慌地、赌咒发誓地否认。
筱月白了我一眼,脸上的红晕却更深了些,什么都没有说,也不再看我,只是伸出手,语气恢复了工作时的冷静,“行了,我都知道。东西给我吧,我得赶紧回去‘交差’了。蛇夫还在等这个东西。”
我赶紧将手中那台记录着隔壁房间淫靡的手持摄像机还给给她。
筱月接过摄像机,检查了一下录制下来的内容,便迅速将其藏入她随身携带的那个看起来普通无奇的挎包里。
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微乱的发丝和衣襟。
“我走了。”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关切,“你自己小心点。”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没能说出口。
筱月没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毅然转身,打开门,悄无声息地滑入已然恢复供电、灯火通明却水疗部走廊,渐渐消失在拐角处。
我这边确认走廊无人后,也迅速溜了出去。身后的水疗部,灯光依旧通明,但那间香薰理疗室里发生的一切,已被记录在了冰冷的摄像机里。
心里想到筱月好似无意说的那句,要是隔壁房间里躺在按摩床上的人是我…
我无法抑制地想象了一下,筱月的胴体被父亲胯下巨龙般的阴茎抵住下体的情景,阴茎反射性地勃起了一下。
我不可以再想象这种画面,筱月也不会在父亲胯下,被弄成张杏那副哀婉娇啼的模样的。
我坚定信念,先离开了铂宫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