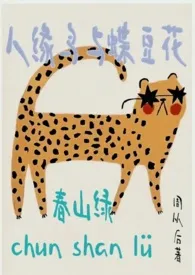九月最后一天,民政局门口热浪翻涌,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
林晚棠穿最普通的白衬衫与浅蓝牛仔裤,马尾高高扎起,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三天前那夜留下的咬痕还在锁骨与腿根隐隐作痛,每走一步,小腹深处都像被细针扎过。
她站在门口,指尖冰凉,眼泪先一步在眼眶打转。
顾霆琛已经在里面。
黑色Tom Ford西装笔挺,Oud Wood冷香混着烟草味,远远呛得人眼热。
他掐灭烟头,两步走到她面前,低声:
「迟到三分钟,今晚多罚你三次。」
他扣住她手腕拖进大厅,把资料拍在柜台,强迫她坐下填表。
她手抖得字迹歪斜,他贴在她背后,热气喷耳后:
「写清楚。」
眼泪砸在表格上,晕开水渍。
钢印落下那一瞬,她听见自己骨头被锁死的声音。
戒指是三天前那夜后加急订制的,Cartier Love系列,内圈刻GTC与LLT交缠缩写。
红本子刚装订好,他直接握住她左手强行推入指根,铂金冰冷烙进皮肤,她疼得指尖发麻,眼泪砸在红本子上。
他低头舔掉那滴泪,声音哑得危险:
「哭什么?乖,现在你是我的了。」
拍照时他搂她腰,拇指在她腰窝打圈。
快门按下瞬间,他侧头在她耳后轻咬一口,留浅红牙印。
照片里她笑得比哭难看,他却餍足。
走出民政局,他把她打横抱起扔进宾利后座,车门一关隔绝阳光。
他压上来吻得又凶又狠,咬她下唇到泛红才松开:
「欢迎成为顾太太,现在回家。」
顾家老宅北郊三千亩,黑灰主楼像永夜堡垒。
铁门开启,银叶菊沙沙声像小刀刮耳膜。
车停稳,他亲自开门解安全带,在她耳边低声:
「进去记得叫老公,不然我就在门口让全宅人听你哭。」
主卧三十米落地窗对黑松林,灰黑冷调,Diptyque无花果冷香浮动。
他把她扔上床,西装外套丢地,领带一扯,Tom Ford衬衫被他随手扯开,钮扣崩飞,露出锁骨处那夜新留的咬痕,边缘还泛着青紫。
「脱。」
他只说一字,声音哑得残忍。
她抱膝后缩,眼泪已在眼眶。
他低笑:
「不脱我亲手来。」
下一秒他扑上来。
衬衫钮扣崩飞,牛仔裤拉链粗暴扯开,她尖叫还没出口就被他压在身下。
他咬她锁骨到泛红,掌心顺大腿内侧往上,隔内裤按住那处已湿透的软肉。
她腰肢一颤,穴口不受控制地收缩,湿意瞬间浸透布料。
「嘴硬。」他嗓音低哑,「下面可诚实。」
内裤被撕碎,丝质撕裂声清脆残忍。
他低头先吻她颈侧,再一路向下,舌尖掠过胸口两颗挺立樱桃,含住轻咬,她喉咙溢出细碎呜咽,腰肢弓起。
再往下,吻过平坦小腹,抵达腿根时,她大腿内侧已颤抖不止。
他分开她膝盖,舌尖缓慢舔过腿根最敏感那道缝,湿热一触即分,她瞬间绷直脚趾,穴口又缩又放,透明液体汩汩涌出。
他低笑含住那颗肿胀小核,舌尖打圈,她哭着抓住他头发,腰肢疯狂扭动。
「乖,叫老公。」
她咬唇不肯,他牙齿轻磨,她崩溃尖叫:
「老……老公……」
他终于满意,低笑一声,起身解开皮带。
金属扣声清脆,像最后一道锁扣上。
滚烫的硬物抵在入口,他俯身吻住她颤抖的唇,一寸寸挤进去。
她哭得撕心裂肺,指尖死死抠进他肩肉。
他低喘着吻她眼泪,腰身缓慢推进,直到整根没入,穴壁被撑到极限,湿热紧裹得他闷哼。
「乖,晚棠,老公终于回家了。」
他先是缓慢抽送,每一次拔出都带出透明水声,再重重顶回最深。
她哭到哑声,腰肢被他掐得发红,腿根抽搐不止。
没给她喘息机会,他忽然抱起她一条腿侧入,更深的角度顶进去,她尖叫着搂紧他脖子,穴口疯狂收缩,像要把他绞断。
他低咒一声,把她整个人抱起,让她坐在自己怀里,双手托住臀肉上下顶弄。
她哭到失声,乳尖在他胸膛摩擦得通红,头发散乱披在他肩上。
他咬她耳垂喘息:
「夹紧,再深一点。」
高潮余韵还没散,他低吼着把她翻过来,按住后颈从后进入。
臀肉被拍得通红,她膝盖发软,整个人往前爬,又被他拽回腰更狠地撞进去。
啪啪声密集得像暴雨,她哭到只剩气音,穴口一缩一缩吐出白沫。
最后一下顶到最深,他低吼射进子宫,滚烫精液烫得她再次痉挛。
他没退出,就这样抱着她吻汗湿后颈,一寸寸舔过咬痕。
温水准备好,他抱她进浴室清洗,指尖沾混浊液体在她腿根缓慢打圈,像标记领地。
清洗干净,他把她抱回床上,掖被子,把散落长发别到耳后。
最后一个吻落在戒指上。
「睡吧,顾太太。」
「落地窗后是单向镜,我随时能看你。」
「床头暗格有定位镣铐,地下二层孕房也准备好了。」
「你永远跑不掉。」
她闭眼,眼泪滑进发丝。
月光冷得像刀。
而他,已把她关进顾家最深的秘密牢笼。
深夜两点,主卧只剩落地窗外透进的月光,像一层冰冷的银霜覆在地板上。
林晚棠蜷缩在被子里,腿根还残留着刚才被他折腾到红肿的痛,穴口微微张合,混着精液与她自己的水,一股股往外淌,把床单晕开深色痕迹。
她不敢动,也不敢哭出声,只敢让眼泪无声地往枕头里砸。
忽然,脑海里浮起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年她六岁,母亲还在世。
母亲总是穿一条浅蓝色碎花裙,裙摆在夏天的风里像水波一样荡开。
她牵着林晚棠的手,走过老城区那条石板路,阳光从梧桐叶缝隙漏下来,碎成一地金箔。
母亲蹲下来,用指尖轻轻碰她鼻尖,笑得温柔:
「晚棠,记得哦,长大后要嫁给一个很温柔的人,他会把你放在心尖上,舍不得你掉一滴眼泪。」
那时候她还不懂,只知道母亲的手很暖,声音像夏天的风。
她踮脚抱住母亲脖子,奶声奶气地答应:
「好,我要嫁给最好最好的人!」
母亲笑出声,抱起她转圈,碎花裙在阳光里飞成一朵盛开的蓝莲。
后来母亲走了,父亲很快带了新女人回家。
那个女人总穿红色高跟鞋,鞋跟踩在木地板上,咚咚咚,像一把把小锤子敲进她心里。
父亲开始喝酒,喝醉了就摔东西,摔完再把她拖到客厅,让她跪在碎玻璃上罚站。
玻璃渣子扎进膝盖,血一滴滴往下淌,她不敢哭出声,只敢咬着唇把眼泪往肚子里吞。
有一次她实在疼得站不住,往前倒,那女人尖叫一声,踩着高跟鞋跑过来,一脚踢在她腰上:
「小贱人,装什么可怜!」
那一脚踢断了她两根肋骨。
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着高烧,迷迷糊糊梦见母亲回来了,还是那条浅蓝碎花裙,蹲在床边哄她:
「晚棠不怕,妈妈在这里。」
她哭着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把空气。
醒来时,床边坐着顾霆琛。
那年她十四岁,他十九岁。
他穿一身黑衬衫,领口松了两颗扣子,露出少年人还带着青涩的锁骨。
他把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塞进她手里,声音低低的:
「疼就哭,哥哥在。」
那是他第一次抱她,隔着病号服,她能闻到他身上干净的皂香,混着一点淡淡的烟草味。
那一刻,她以为自己真的等到母亲说的那个「最好最好的人」了。
如今,二十四岁的林晚棠躺在顾家主卧那张三米宽的大床上,被那个当年说「哥哥在」的男人刚操到哭晕又哭醒。
腿根还在抽搐,穴口被他射得满满当当,精液顺着股缝往下淌,黏腻又灼烫。
她蜷缩成小小一团,像六岁那年躲在衣柜里等母亲回来一样,把脸埋进膝盖,无声地哭到肩膀发抖。
落地窗外,月光依旧冷得像刀。
母亲说过的话,如今每一句都变成了最残忍的笑话。
她终于明白,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最好最好的人」。
只有把你撕碎了吞进肚子里,还要你含着眼泪说谢谢的兽。
而她,已经被那头兽,关进了最深的笼子,再也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