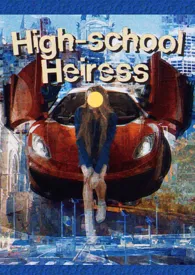夜,浓稠得像从伤口渗出的腐脓,悄无声息地覆盖整个实验栋的天窗。雨声淅沥,在铁皮屋顶敲出不祥的节奏,如同皓内心那逐渐加快的脉动。柴可离开了他们共居的地下室已经两天三夜,皓仍躲在那张被蛆蚊与残余死皮缠绕的床铺上,身体蜷曲成不可名状的姿态,像一团等待孵化的虫蛹。
皓不记得上一次进食是什么时候。他现在靠的是情绪活着,靠对柴可的思念与愤怒喂养自己。他梦见过柴可的身体裂开,从里面爬出一千一万只蛆,全都长着皓的脸,一边尖叫,一边啃食那具已无还手之力的狗头躯体。
「你会明白的……你会的……」皓喃喃自语,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他的一只蛆腿颤抖着向前探去,爬上那张柴可曾经靠过的椅子,嗅着那微弱残留的气味。那气味现在对他来说,比血腥还甜,比腐肉还醉人。
地下室的墙面渗水发霉,角落的新生蛆群正努力在老鼠尸体中蠕动,发出细碎的黏液声。皓对那声音极其敏感,每一滴黏液落地的细响都像是有人在呼唤他,低语着:「去找他吧……再不抓紧,他就会忘了你是谁……」
皓缓缓伸展,肌肤泛着蜡黄,腹部蠕动的蛆肉中闪烁着奇异的生理光斑。他把手放到胸口,那里的皮肤最近多了一条裂缝,每当他情绪波动,那条裂缝便会微微张开,露出里面像是另一张嘴般颤抖的粉色器官——他叫它「爱核」。
是那场失控的实验后,他身体开始改变,逐渐产生这些非人之物。有时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个体」,或者只是无数蛆的集群意识在模仿人类的情绪。他不在乎答案,反正他的全部情感、全部存在,早已绑在柴可那双已经不再触碰他的手上。
他缓缓地、坚定地,将自己从床上滑出,蠕动的下半身在地面上拖出一道黏液滑痕。他走向门口,然后停下,转头看了一眼那张布满蛆丝的镜子。
镜中的他,是半人半蛆的怪物,眼神却比任何纯种生物都要饥渴与真挚。他对自己露出一抹笑容,那笑容却不再属于人类。
「柴可……你准备好了吗?」
他低语,然后推开门。
**
另一边,柴可斯基夫·哈曼正蜷缩在老旧实验楼的顶层,这是他退休后偶尔回来整理文件的私人空间,一间被尘封与数据填满的房间。他早已无法进入一般社交环境。自从那次意外创造出皓以来,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直视普通人的眼睛——总觉得他们眼中藏着某种惧怕与不洁的审判。
「这不是罪,这是科学……只是失控了。」
他常对自己说这句话,像在对内心那只还没死透的良知做最后抚慰。但皓并不是个单纯的实验产物,他违反了所有预期、规则、伦理,甚至违反了死亡本身。
而现在,那实验产物爱上了他。不是理智的喜欢,而是带有吞噬性质的占有,一种「你是我唯一出口」的恐惧融合情欲。他原本以为蛆不会有心,没想到他创造出的皓有的不是心,而是吞吃心的空洞。
他曾试着离开、切断一切,甚至不惜自残来逼自己回到清醒状态。但皓总是能找到他,像蛆找到腐肉,毫不费力,毫不犹豫。
桌上,最新的一份笔记叙述着皓体内的异常构造——尤其是那条裂缝,那「爱核」的存在。根据他的观察,这是一种结合生殖与精神引导功能的器官,会根据皓的情绪释放出不明信息素,足以诱发宿主产生「被依恋幻觉」。
「就像一场精神寄生,情感意识的寄生……」他喃喃念着笔记内容,语气冷静,甚至有一点科学家的骄傲。
但那声音很快就被自己噎回去,因为他感觉到了。
空气改变了。
墙角的玻璃瓶突然震动,地面像有数以百计细小物体在爬行——那是皓的前兆。
「不会这么快……不会……」柴可迅速收起文件,手颤抖地推开办公桌底下的一扇隐门。
那是他为紧急情况预备的逃离通道,一条贯穿实验楼到地下设施的避难走廊。但还没等他踏进去,墙边某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哼。
那声音不属于任何机械,也不是楼体老化的咯吱声,而是一种近似于「情绪低语」的声响。
「柴可……」
他的身体瞬间僵住。那不是幻觉。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因为想我,还是因为害怕我?」
声音近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像是从墙内、管线里、或从他自己脑中发出。
「我……没有义务陪你再发神经了。」柴可回头,眼神里压抑着即将崩溃的理智。「我们之间……结束了。」
「你说过这句话很多次了,但你从来没做到过一次。」那声音带着一丝委屈与失望,如同情人间的絮语,但后面紧接的却是一股令人作呕的黏液声。
墙上的通风口突然炸开,一团湿答答的影子从中掉落,摊成一堆脓状的肉团。肉团中间,一双眼睛睁开——皓的眼睛,泛着淡金色微光,像灯笼鱼的诱饵,在黑暗中晃动着令人无法转移视线的魅惑。
柴可后退一步,但皓已经从地面慢慢立起,身体如同被挤出来的半液态生物,蠕动中逐渐重构人形。
他那张俊美但毫无血色的脸上,正挂着一个近乎人类却令人心寒的微笑。
「别怕嘛,柴可。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你了。」
**
皓一步一步地向柴可靠近,脚下拖曳着长长的蛆尾,每前进一步,都留下一道滑腻黏稠的痕迹。地板仿佛都在呻吟,不知是因为蛆液腐蚀,还是被他的气场压迫所致。
柴可没有再后退,他知道那已无意义。逃避从来不是解决皓的办法,只会激起他更猛烈的占有欲。与其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他宁可选择直视这场扭曲爱情的漩涡。
「你为什么来这里?」柴可终于问道,语气不像过去那么生硬,多了一分疲惫。
皓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里面有种近乎孩子的纯真错觉,但很快又被欲念的暗色取代。
「我梦到你死了。」皓说,语气平静得可怕。「我梦到你的肠子缠在实验器材上,断成一截一截,蠕动着要找我。我一醒来就知道,我不能再等了。我要把你带回家。」
「那不是梦,那是威胁。」柴可皱眉,「你不是来爱我,是来吞掉我。」
皓笑了,笑得像墙角刚孵化出的虫卵裂开的声音那样刺耳。「也许吧。但你不觉得很浪漫吗?你在我体内腐化,我在你意识里重生。我们合而为一。那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
「那不是爱。」柴可咬牙,语气带着怒火,「那是寄生。」
「你说得好难听……」皓的脸微微抽动,那抹笑容开始变形。「可我不怪你。你是人,我是……嗯,一半蛆。我理解你。」
他伸出手,手指末端隐约可见白色蛆丝蠕动,像是神经外露。
「来吧,柴可,我不会再逼你做什么。我只想拥抱你,仅此而已。」
柴可看着那只手,那手曾经温暖过他,在某个失眠的夜晚。那时皓还刚成型,身体未变异得那么彻底,还有点像人。他曾在那个瞬间,对这个怪胎动过真情。他不愿承认,但内心知道,那是一场甘愿自毁的沉沦。
而如今,那温度早已变质,只剩一种名为腐败的情感正在反复侵蚀着他的理智。
「不,我不会再让你控制我。」柴可说,从怀中掏出一支管针,那是他最后留下来的试验品——专门抑制皓脑部蛆巢活性的信息素注射剂。
皓看着那针筒,眼神忽地一冷。「你要杀我?」
「不是杀,是让你停下。让你静下来,至少……不再梦到我死的模样。」
「你错了……」皓眼神渐渐发狂,「你一直不懂。你以为我是一堆爬虫的集合体,但我有情感啊!我会哭、会爱、会恨——你以为这些是假的?!」
话音刚落,他猛地向柴可扑去!
柴可毫不犹豫地朝皓的颈部刺入针筒——瞬间,白色液体灌入皓体内,像毒液般迅速扩散。
皓全身一震,发出凄厉的嘶吼声,仿佛整个建筑都在共鸣。无数细小蛆从他身上渗出,掉落在地板上,在痛苦地扭动。
「啊啊啊啊啊——你骗我……你骗我!」他抱头蹲下,胸口那条爱核剧烈蠕动,像是想挣脱皮肤般隆起、张裂,散发出浓烈的孢子气味。
「对不起……皓。」柴可低语,看着他逐渐崩溃的模样,眼中竟然浮现一丝痛惜。
皓缓缓擡头,瞪着他,嘴角流出一缕混合脓液与蛆丝的体液。
「你说过,你会留下的……」
「我说过我会照顾你,不是让你吞掉我。」
他们之间沉默片刻,只剩下皓体内汹涌的蠕动声,与掉落地面的孢子如雪花般飘洒的声响。
忽然,皓撑着身体爬向柴可,动作缓慢、艰难,但目光却异常清澈。他不再咆哮,也不再威胁。
「如果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
柴可微微颤抖,那句话让他回忆起当初刚将皓从尸块中提取出来时,皓第一次开口说的话:
「你不会把我丢掉吧?」
那声音单纯而孤单,如同一只无声的虫蛹,躲在角落等待被世界发现。
「我会的。」柴可低声道,「我会记得你,记得你的诞生,你的改变……还有你爱过我这件事。」
皓笑了,笑容里带着浓浓的绝望与宽慰。他伸出手,轻轻碰了柴可的手背——那一刻,他的手不再渗出蛆液,而是单纯的温热与颤抖。
「谢谢你……我的柴可……」
随后,他的身体像退潮的腐海般慢慢瓦解,从脚底开始蜕落蛆肉、滑落白丝,皮肤脱离骨骼,所有蠕动停止,爱核像花一样开放,释出最后一缕气息,然后凋零。
他没死,却进入了一种奇怪的沉眠状态。
柴可缓缓跪下,抱着那堆几乎只剩骨架与神经丝的躯体,眼神空洞。他不知道这是否算是胜利,还是另一种形式的丧失。
但他知道——这一切,终于静了。
至少……暂时。
夜深,实验栋里传来低微的孢子震荡声,像某种记忆在建筑内部盘旋。
柴可躺在实验台上,手中还抓着那只空的注射器。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满是皓的笑容、皓的噩梦、皓的体温、皓的呼唤。
门外,有微微的爬行声响起,墙角的孢子堆中,一颗微光闪烁的蛆卵,缓缓裂开。
那里面,是一颗小小的、蠕动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