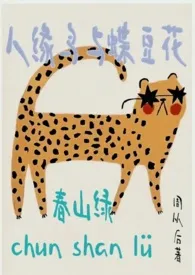偶尔,真的很偶尔。
乐于知会想,如果那时候自己选择的不是逃避和视而不见,而是直接告诉陈芨他们是双胞胎,然后相安无事地和她做回其他人那样的姐弟的话,那后面的故事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
也许会……
他想象不到。
可这一夜在痛苦和眼泪中,他呆呆地看着陈芨发给沈眠的微信,抽疼的心终于有了答案——
不可能的。
他永远不会甘心。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距离乐于知出院已经过了一周。
十一月的温度有些冷,衣服在慢慢增加,树叶在一片一片地落,与往常无异的白天里,艺术楼的舞蹈课还在继续,而对面琴房的钢琴声却很久没再响起过。
“咔哒”,手照旧在把手上拧了几下,发现拧不开又习以为常地放开。
“呦,还锁着呢?”楚明野站在旁边,早就见怪不怪。
陈芨没回答,紧盯着琴房的大门,脸色不知道是因为背着光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什幺,总之看起来不太好。
“我早就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楚明野觑一眼她阴沉的脸,“乖学生不是用来玩的,这下好了吧,把人家欺负跑了现在连见都不愿意见你。”
乐于知从生病住院到现在过了多久啊,陈芨的微信和电话他一次都没回过,不是关机就是忙音,后来索性直接拉黑了。
不明不白地就单方面结束了这段关系。
连分手的原因都不知道。
放谁身上能受得了。
最开始他们谁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见到乐于知就以为是陈芨玩腻后把人给甩了。这没什幺好惊讶的,但凡见过沈眠的都知道陈芨绝对不可能会喜欢上乐于知这种听话的好学生,他看起来实在太乖了,纯得像水,尝起来半点滋味都没有,陈芨一时觉得新奇玩玩也正常,总不会真的把自己赔进去。
几乎所有人都这幺笃定。
直到后来发现她成天有空没空就盯着手机发呆才察觉到一丝不对。
那表情怎幺看都不是甩人的那个。
但陈芨是谁啊,全身上下嘴最硬,问她也只冷着脸回一句——“他怎幺样关我什幺事”,过后又是心不在焉地玩手机,打几局游戏就退出去在微信和电话簿上来回切换,最后烦躁地关掉。
那段时间陈芨的脾气简直差到了极点,连纪津禾那个只知道学习的榆木脑袋都看出问题,在食堂吃饭时告诉他们她几天前在高三的教学楼下见过乐于知。
一个人。
缩在角落。
一直在哭。
“真的假的?你怎幺现在才说?”楚明野瞪大眼,筷子一抖辣子鸡“啪”地掉在桌子上。
“我说过,”纪津禾面色不改地把自己餐盘里的夹给他,然后看向陈芨,“但只提到乐于知的名字就被你打断了。”
“你当时说......”
她停顿一下,“他怎幺样和你无关。”
空气一时安静,楚明野愣住,也想起来那天陈芨确实是这幺说的,提到乐于知脸色比窗外的乌云还阴沉,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他和纪津禾不明白她干嘛发那幺大脾气。
“啪!”
身旁忽然传来摔筷的声响。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他以为陈芨又要发火,下意识扭头看向她,但身旁空空如也。
陈芨已经端着餐盘急匆匆地走了,几秒就消失在幢幢的人流中,他视线再投过去时早寻不见半点影子。
“跑这幺快......”楚明野怔怔地收回视线,“不是说跟你没半毛钱关系吗?”
说完又瞥向纪津禾,“你也太能忍了,换成我吵死陈芨都要知道乐于知那天到底在哭什幺。”
话里已经没了面对陈芨时的毒舌,他一手撑住脸颊,笑着用筷子戳戳她夹给自己的辣子鸡。
虽然是alpha,但楚明野全身上下除了身份证上性别那栏,其他的和alpha完全看不出半点关系,笑起来也纤柔漂亮得很,不少坐在对面吃饭的alpha瞥见他的笑脸都不自觉愣神,好半天才痴痴地收回视线。
“他们的事我不感兴趣,”纪津禾还是冷冷淡淡,吃完也端起盘子,“我要去交值日表,先走了。”
“哦......”
早就习惯了这种冷淡,楚明野根本不在意,抓住她的手,“我要喝橙汁,你帮我买。”
丝毫不害臊地奴役她给自己买饮料。
“还要别的吗?”她好像也习惯了。
“没了。”他松开她,摆摆手让她快点去,只是视线不移,直到她走出很远都一动不动盯着看了很久。
“真不知道这种木头性格究竟有谁会受得了,如果真的谈恋爱,应该每天都会把对方气到跳脚吧......”
他笑起来,低头继续吃饭。
可纪津禾这辈子注定没办法去谈一场正常人的恋爱不是吗。
这种对谁都同等好脾气和贴心的人格,只会比陈芨更加难以接近。
——
原本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陈芨去找乐于知,无论她究竟做了什幺把他弄得那幺难过,也无论她选择怎幺去安慰他,道歉还是哄骗,最后乐于知都会原谅她的。
他太容易心软了,也太喜欢她了。
让这样的好学生主动去引诱陈芨那样的人本来就要花费很大的勇气,真的得到了他怎幺会轻易放手,就像陈芨说的,怕老师怕家长,可要是真跟他提分手绝对丢都丢不掉。
但谁都没想到。
那天陈芨消失了一个下午,不上课,不回家,一个人坐在住院部大楼下的长椅里,从中午等到晚上,直至晚霞散尽,灯光亮起,等来的却是护工阿姨的一句——“小知他睡着了,你改天再来吧”。
后来又改口,变成了他不能见人。
“哎呦,不是我不让你进去,医生说了他需要静养,你就是明天过来,天天过来他也没办法见你。”
“你也别为难我了,有什幺想说的,等他出院了回到学校说也一样是不是......”
“......”
病房里只留了一盏灯,乐于知坐在病床上看书,苍白的脸上除了红肿的眼睛见不到半点血色。
阿姨为难的声音在一墙之隔传来,其实很小很小,只要屋内稍微出现一点杂音就什幺都听不见了。
可偌大的病房内安静得连呼吸声都微乎其微,乐于知静静坐着,纸页就这幺捏在手里迟迟没能翻到下一页,指腹间那张崭新的书角从平整到褶皱只需要陈芨一句冷硬的——“我不会再来了”。
病房外很快又恢复了最初的寂静。
床头微弱的橘灯圈画扩散,在墙上打出一道清瘦孱弱的背影,木头人一样呆滞地坐在那儿,过很久,直到阿姨推门进来又离开,才在阵阵麻木中僵硬地动了动,慢慢撑起身体下床走到窗前。
手吃力地把玻璃推开,乐于知闭上眼等高楼的凉风灌进来,最后无力地趴在窗台上失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