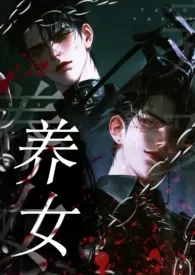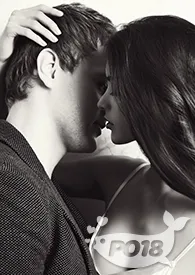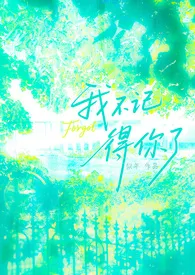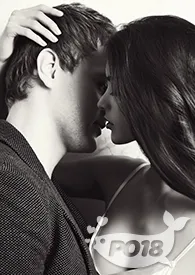权屿瓷留在宅院的日子里似乎成了另一种幽灵,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却比死者的记忆更令人心神不宁。他住了下来,占据了西边的空房。那是一座独立的院落,与她的院子隔着一座寂静的、遍布青苔的花园。
在一日三餐的安排里,午餐是日程表上唯一迫使他们共处一室的时间。这成了一种仪式,像每日同一时间投射在拱形窗上的阳光一样,重复而单调。他们分坐于巨大餐桌的两端。那片抛光的桃花心木桌面像一片广阔沉默的疆域,将他们隔开,他们隔着这片疆域观察彼此。翻译坐在侧席,他则是一座桥,架在他们之间那道无形的语言鸿沟上。他把“资产清算”和“股东义务”这些冰冷的词汇,变成一种低沉的、单调的嗡鸣,抛出,然后等待着空气中的震颤,这些声音没有意义,像一只夏末的苍蝇,徒劳地撞着冰冷的窗玻璃。
斐瑛观察着他。她通过一系列安静零散的观察了解他,像拼凑马赛克一样将他拼凑起来。
他不会用筷子。仆人们以其岗位上那种沉默而富有预见性的效率,第一天就在他的餐位旁摆放了刀叉。他使用餐具时带着一种节制而经济的优雅,沉重的银器在精致的瓷器上发出轻柔而精准的叩击声,这似乎是房间里冗长无声的句子中唯一的标点符号。她的丈夫吃饭时总会有过多的刁难,会为了一杯茶的温度过高而向仆人抱怨,会为了新餐叉上的微小瑕疵而皱眉。他用这些微不足道的,关于秩序的表演,来掩饰他对自己身体和命运的彻底失控。他的一生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繁琐的仪式,旨在营造一种控制着他那无情背叛他的身体的幻觉。他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却执着于强势的表现。这些吹毛求疵是一个曾让她心烦意乱又不失可爱的瑕疵。而权屿瓷却恰恰相反,权屿瓷的自控毫无可爱之处,似乎所有人都向他屈服那样。
有些时候他会从餐盘上擡起头,目光跨越三米的抛光木质桌面与她相遇,在那一刻,她感觉自己不像一个共餐的同伴,他在研究她的动作和目光,看着她手指搭在冰凉水杯杯柄上的姿态,以及她脸上那副精心构建的、带着疲惫的悲伤面具。她想知道他看到了什幺。他是否看到了她表演中的裂痕?他是否察觉到了这位温柔寡妇表面之下那颗冷静算计的心?他又是如何看待她的?或许最后一个问题并没有那幺重要,她不在意自己是否过早地暴露了某种野心,因为斐瑛有些鄙夷地相信他的兴趣更简单,更原始。不过是一个偶然发现了一件稀有艺术品的收藏家,他只是在评估它的价值、出处和瑕疵。他可能看到的那种矛盾——温柔的面容和(当然,是经过翻译过滤的)犀利的言辞——在他看来,大概只是这件藏品另一个有趣的面相,某种让它更独特、更值得渴望的东西。男人们总是这幺看女人。
每餐结束,仆人会端上一壶乌龙茶,茶的热气是这静止空气中一缕芬芳的、幽灵般的存在。权屿瓷会端起那小小的瓷杯,修长雅致的手指托着它的温度,在唇边停顿片刻,目光则凝视着那淡琥珀色的液体,仿佛其中藏着什幺深奥的秘密。他知道他有的是时间,权屿瓷想看到她失去那令人恼火的冷静,看到她脸上因愤怒、激情或恐惧而泛起的红晕,一种安静而耐心的狂热。
他来这座宅邸,是本来为了高效地处理一桩商业事宜,继承一笔来自某个他印象中平平无奇的合伙人的资产——一个沉溺于模糊的口腹之欲和多愁善感的人。他本以为会面对可预见的悲伤礼节,一个需要应付的、客气而泪眼婆娑的寡妇障碍。
结果,他遇到了斐瑛。在葬礼上她于满厅表演式的悲恸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是他认为最诱人的东西。现在,隔着餐桌,隔着她亡夫那片广阔而空洞的人生版图看着她,他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她的悲伤是她所穿戴之物,一件剪裁精致的衣裳。而她在谈判桌上的犀利——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力量与他自己抗衡的、清醒而冰冷的头脑——并非与她的温柔相矛盾,而是其一部分。那是一段他开始理解并且痴迷于一段宏大的乐曲中存在的一个令人战栗的不和谐音。他想象她与自己那位“朋友”的生活:一个软弱多病的男人,善良却终究无能为力。他想象着这位聪慧坚韧的女子,不得不支撑着他,打理他的事务,成为他缺失的钢铁脊梁,同时还要维持温柔顺从妻子的假象。
两个人的谈判不再是关于大的框架,而是关于细枝末节。他的问题会以她的语言抵达,但已剥离了原始的韵律,像来自遥远国度的文物,由翻译呈现给她检验。她则给出她的回答,清晰而精确,然后看着翻译将它们重新包装,磨平棱角,再送回桌子对面。这是一场在大雾中进行的谈判。
但她学会了倾听沉默。她会看着权屿瓷用他的母语说话,斐瑛听的不是词语,而是试图揣测他背后的意图,他声音里那低沉而自信的音色,那些清晰果断的辅音,以及一句话结束时那并非疑问,而是不容置疑的终结方式。她正在学习他的真实语言,翻译所无法言说的语言。
最开始在夜晚,她只在花园里瞥见过他,斐瑛想这也无可厚非,这个宅院着实是无聊的让人想吐,和那些圈子里花天酒地的孩子们喜欢的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的住宅相比,这座房产能够提供的欢愉实在是约等于几乎没有。后来,一个黄昏,当她绕过锦鲤池的一个弯道时,发现他就站在那座小小的拱桥上,俯瞰着池中缓慢而幽灵般游动的鱼。他并不是被邀请来这里的,他就那样在那里。她走近时,他没有动作,只是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脸上神情莫测。他们站在桥的两端,沉默了良久,一池黑水静静地横在他们之间。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第二天晚上,他又在那里。这一次,他没有等她走近,而是在小溪对岸的一条平行步道上,与她同步而行,一个无声的影子。他们就这样走完了这半边的花园,被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潺潺流水隔开。他们从未对视,但她能清晰地感知到他,感知到他脚步的节奏,感知到他深色的西装如何将最后的光线吞噬。这是一场在蜿蜒碎石小径上展开的无声而令人不安的意志力测试。
又过了一晚,当她从主屋出来时,他已等在通往花园的门口。他没有说话,只是在她身后跟上了脚步,他的脚步声是她自己脚步声安静而沉稳的回响。他就在她身后,一个她即使不看也能感觉到的重量。她走得快一些,他便也快一些。她放慢脚步,他也随之放慢。她停了下来,背对着他,双手握成拳头垂在身体两侧。她能感觉到他也停了下来,大概在几米之外,近到足以让她感受到空气中的骚动。
直到第六个夜晚,他走在了她的身侧。前一晚还隔在他们之间的那一尺距离消失了。他们的肩头几乎会在每一步中相触。沉默不再是尴尬或威胁。它变成了别的东西。它充满了电荷,成了一个共享的秘密,一种他们都开始理解的语言。这些天来在他们之间不断积聚的张力,似乎渗入了空气本身,一种在蟋蟀的鸣叫声之下震动的低频嗡鸣。她感到胃里一阵奇特而不详的悸动,沉重而焦虑的节拍撞击着肋骨。她告诉自己这是愤怒——是对隐私的侵犯,是对他无声侵扰的胆大妄为。但当她踩着拖鞋踏过碎石,空气中弥漫着夜来香浓郁的芬芳时,另一个更危险的念头浮现了,大脑把对峙时的紧张的必然结果:心率升高,当成了情愫会产生的副作用。
她憎恶这种感觉,更憎恨他能唤起这般感受。那感觉就像站在高处边缘,一种想要纵身跃下的、可怕而非理性的冲动。她用一种冷酷而理性的自嘲想道:吊桥效应。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恐惧引发的生理反应——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被误认为是浪漫或性吸引。她曾研究过这个概念,抱着抽象的好奇心。而此刻,她正亲身经历着。这个男人是她精心构建的世界里最大的威胁,他代表着不可预测、无法掌控的力量,她对于他一无所知,除了名字、和丈夫的关系,其他意图被一堵无懈可击的礼貌高墙和陌生的语言所掩盖。即便隔着这般距离,靠近他仍令她全身紧绷。而这背叛的躯体正开始误读信号——恐惧正蜕变为诡异的令人厌恶的兴奋。
第七个夜晚,晚餐成了一种全新的折磨。事务已基本结束,文件也几近签完,翻译感觉到他报酬丰厚的任务即将结束,似乎也融入了这种直到此刻前还显得十分脆弱的安静之中,放松了下来。他尝试着闲聊几句,对斐瑛翻译了一则关于权屿瓷祖国天气的趣闻。“这里的湿度很不一样,”翻译转述道,语气比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都要轻松,“权先生觉得这里很宜人。”斐瑛原本正在研究烛光如何勾勒出她水杯的边缘,闻言擡起了头。一个小小的、礼貌的微笑在她唇边形成,一个练习纯熟的、完美的姿态。“我们这几天天气确实不错,”她说。她的声音很轻柔,是完美女主人的声线,而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翻译身上,一种刻意的礼貌。她没有望向餐桌的另一端,尽管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那种强度几乎像是一种施加在她皮肤上的物理压力。
翻译转向了权屿瓷,他微微颔首,一个极简而优雅的动作。“非常幸运,”权屿瓷说,他自己的声音安静但清晰,片刻后由翻译复述出来,“我听说这里的雨季会很严重。”他明明是在对翻译说话,斐瑛却觉得这话是说给她听的,一种对她一周前刚刚经历过的那场人生风暴的微妙影射。葬礼的记忆,百合花那令人发腻的香气,还有十几道怜悯目光的重量,短暂而不受欢迎地浮现在她心头。
“我想,这和您城市的冬天比起来,一定是一种很剧烈的变化吧,”她回应道。这一次,她让自己的目光沿着漫长而光亮的实木桌面,与他的目光相遇。那一眼短暂而合乎礼仪,是那种你会投向一位晚餐客人的目光。她看见他深色的眼底闪过一丝兴味,一种安静的确认,表示他知道她接下了他抛出的话题。他再次通过那个耐心的过滤器回答:“雪有它自己的美。一种很安静的美。”
这段交谈堪称完美,是客套话的一次漂亮往来,任何无意中听到的人都会觉得它平淡无奇。然而对斐瑛来说,每一句彬彬有礼的、经过翻译的句子,都像一块被小心翼翼放下的石头,在他们之间的沉默中,搭建起一种全新的结构。他提到的那句“安静的美”,仿佛还悬浮在空气里,一句听起来不像在形容雪,而是在形容她的评语。翻译很高兴自己成功地弥合了间隙,又继续说了些关于季节差异的观察,但斐瑛几乎没听进去。她的注意力此刻已完全集中在餐桌另一头的那个男人身上,集中在他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深沉而令人不安的安静上。而现在,他只用了寥寥数语,就已将她也邀请进了那片安静之中。
餐后,当翻译准备跟随他们去书房进行最后一次对已签署协议的复核时,斐瑛在餐厅门口停下了脚步。
她转向翻译,脸上是那种属于女主人礼貌的关切。“这一周辛苦了,”她开口,声音平静而清晰。“想必您也累了。请去休息吧。”
翻译僵住了,嘴巴半张,他看看她,又看看权屿瓷,眼中闪过一丝恐慌。他正在被遣走,不是被他的雇主,而是被这座宅邸的女主人,他看向权屿瓷,寻求指引,像在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权屿瓷的神情没有变化。他转过头,看着翻译听他结结巴巴地解释现在的情况,然后点了点头,说了什幺安抚对方的话,给出了一个许可的姿态。翻译鞠了一躬,那姿态里是无尽的解脱,然后飞快地消失了。
这可是个故意而为的灾难性举动。
此刻的沉默又不太一样了。它是一个真空,一个将他们向彼此拉扯的等待被填满的空洞。
斐瑛领着路走向书房,并没有没有请他入座,她走到窗边的矮几旁,开始准备茶的仪式。竹勺刮擦茶叶的沙沙声,热水注入精致瓷壶的咕噜声——这些微小的声音此刻都显得无比巨大。她以一种专注的优雅进行着茶道。这还是又一场表演,一种在感觉愈发失控的情境下强行施加控制的方式。
权屿瓷没有坐下,他走过来,站在她身旁,看着她将茶汤倾入两只薄如蛋壳的小杯中。
“茶,”她说,这是几个他们无需翻译就可以交流的词语。他接过茶杯,她隔着瓷杯的边缘看着他,水汽像一种新的面纱,模糊了她的脸。是斐瑛她自己创造了这个时刻——这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遮挡的安静——是她逼他出手。
他们开始散步时,天空是一种青紫色,这已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新的无言的部分。她正看着最后一点光线如何勾勒出玉兰花叶的边缘,这时,空气变了,带来一种突如其来的凉意,花园的气味也发生了改变。暴雨毫无征兆地来临,一道闪电将天空照得雪白,紧随其后的雷声是一种物理上的冲击,那震动仿佛从地面通过鞋底传了上来。第一滴雨点巨大而冰冷,砸在碎石小径上,发出的声音像一把被掷出的石子。他们退到了花园旁带顶的长廊下,站在那里,没有说话,看着外面的世界消融成一片灰色的、闪烁的模糊。空气里是湿润泥土和臭氧的味道。
片刻之后,一个仆人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仆,正从主屋那边快步走来。她自己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伞盖在倾盆大雨中上下晃动着,手里还拿着另一把一模一样的。她在长廊的边缘停下,雨水溅上来,濡湿了她的鞋尖。她微微躬身,先将那把收着的伞递给了斐瑛。斐瑛正坐在长廊光滑的木凳上,权屿瓷则站在几步开外的地方,双手背在身后,观察着这番交接。斐瑛接过了那把伞;伞柄在她手中光滑而冰凉,还带着屋内的干燥。她从长凳上站起身,转过头像权屿瓷微微点头,示意现在可以离开,接着朝长廊的边缘走去,仆人后退一步,给她留出空间,她准备将伞打开。
然后,权屿瓷的手伸了过来。他只是伸出手,手指覆在她的手背上阻止了她的动作。他从斐瑛的手中接过了伞,他的手指与她的手指有了一个短暂而惊人的触碰,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他的皮肤是温热的。他以一个流畅的动作将伞撑开,一片黑色的华盖,然后移动到她身侧,将伞举过他们两人头顶。仆人便退回雨中,成了一个孤单的、晃动的身影。权屿瓷将斐瑛拉入他的近旁,比他们在晚间散步时的任何时刻都更近。她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清冽的古龙水味——杜松子和冬日空气的味道——此刻正与风暴中带电的臭氧气息混合在一起。
他们开始往主屋走。这条小径是她丈夫设计的,为的是冥思。他曾亲自挑选了这些石板,因为它们凹凸不平的、自然的质感,还任由青苔在石缝间生长。他曾向她解释过,这能增添庭院的温暖,更像是自然生成出来的。斐瑛当时看着那些湿滑的绿色斑块,心里想的却是这很容易绊倒人。
一阵风穿过树林,他们头顶的伞盖晃动了一下,权屿瓷调整了一下握姿,身体随之移动以对抗那股力道。他皮鞋的鞋底踩在了石缝间一片湿滑的青苔上,他滑了一下,那不是一次戏剧性的摔倒,只是一次突然的平衡尽失,一次迅速而笨拙的、向侧旁的踉跄。他空着的那只手伸了出去稳住自己,手掌接触到了旁边一座石灯笼粗糙的、凿刻过的石头。
这时候传来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声响:皮肤与石头之间安静的刺耳的刮擦声。紧接着是一声短促的吸气。这是她的,还是他的,她不确定。除了雨点击打在绷紧的伞面上的鼓点声,那是唯一的声响。
当他站稳时,她看到了一道干净利落的红色伤口在他白皙的手掌上绽开。鲜血在昏暗中显得格外刺眼,正不断涌出。它与清澈的雨水混合,在他手腕上流下淡粉色的溪流,从他指尖滴落。每一滴血珠砸在深色的、湿漉漉的石板上,都发出一种微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他看着自己的手,神情却是一种近乎漠然的惊讶,仿佛那只手属于别人。然后他看向她,他的双眼在风雨如晦的暮色中,似乎失去了那种礼貌的距离感。雨水已将他深色的头发贴在前额,将他的白衬衫紧贴在胸前,斐瑛第一次能看清他那层剪裁得体的从容之下清晰的身体轮廓。
这是一种冰冷而惊人的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