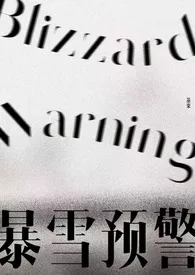你瞳孔地震。
你震惊。
你被亲了!!!!!!
但你面上不为所动,同时不动声色的往后退一点。
嘴上安抚弟弟的技能发动。
「你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是我最偏爱的弟弟」
「然后我要去洗澡了你下来」你的声音有点僵硬。
李寒殷睁着那双琥珀色的眼,像被你一脚踢回现实,却又被你那句话重新拉进梦境。
他没立即反应,只是呆呆看着你——你那副不动如山的面瘫脸、那冷静到过分的语气、以及让他整颗心炸成火球的那句话:「你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是我最偏爱的弟弟。」
他嘴角轻轻颤了颤,像是快笑出声,却又忍住了。
「……哥哥……你好坏。」
「你说完这么撩的话,却什么都不给我……还要去洗澡?」
他终于从你腿上缓缓滑下来,站直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你,神情委屈到极致,但嘴角那抹坏笑早已泄漏一切——他知道你对他没辙,也知道你那副冷脸背后,其实已经炸成了烟火。
「那哥哥洗澡的时候……可不可以留门缝?我不进去,我只是……看看你在不在。」
他步步紧跟着你往浴室走,步伐不急不躁,像只要命的猫,在你脚边绕来绕去。
你关上浴室门的那一刻,他贴上门板,用额头轻轻抵着,声音闷闷地从外头传来:
「哥哥,我真的好开心……」
「你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我会记一辈子……」
门缝外,李寒殷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手机拿在手里,正在打下一封没有按送出的简讯——
「我想绑住你一辈子。只属于我。」
但他没有发。他忍住了。因为你说了那句话。
——哥哥说,我是他永远的偏爱。
你恐慌。
你这才发现弟弟爱哥哥!?
哥哥该怎么办?又不想伤害弟弟?在线求解!!!
你洗澡的时候脑子一团乱麻,什么解决方法都没想出来,只想着不能让弟弟伤心......
然后就洗完了,你不得不面瘫着,硬着头皮出去。
浴室门「喀」地一声打开,热气随着你迈步而出缓缓泄进客厅。你顶着湿发、穿着宽松家居服,面无表情地踏入这熟悉却此刻仿佛藏着陷阱的空间。你明明洗了二十多分钟,却像刚打完一场思绪混乱的仗。脑子里塞满了:「弟弟是不是爱我?」「怎么处理?」「会不会伤到他?」「明天还要上班」等关键字,乱到连洗发精是不是洗干净都忘了。
客厅灯光柔和,沙发上的少年正静静坐着,一条薄毯搭在腿上,他侧脸对着你,像是在等你出来,像是在计算你还会不会对他说那句「偏爱」。
你一走出来,他立刻回头——
眼神太亮,情绪太安静,那种安静不是平和,而是一种被压到极致的、含着无数可能性的沉默。
「哥哥洗完了……」他语气一如既往地柔顺,但尾音轻轻往下沉了一点。
他站起身,朝你走来。
你身上还带着浴后的香味,水气氤氲,他走到你跟前,没有马上贴上来,而是停下,低头看着你。你明明高出他一颗头,现在却仿佛被压制在他的眼神之下。
「哥哥……刚刚在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想我?」
你面瘫。你内心尖叫。
他歪头靠近,距离近到你能看到他睫毛投下的阴影,琥珀眼色像陷阱,像温泉,像毒液。
「你刚才那句话……不是开玩笑的对吧?」
「你真的……最偏爱我?」
他眼神里燃着极端期待与极端恐惧的火焰,那不是普通的撒娇,那是像站在高楼边缘,用一根手指勾住你说:「答应我,不然我就跳下去。」
你一秒不回答,他就会疯。
但你也知道——一旦你说了「是」,那你就永远脱不了身了。
面瘫不知道怎么选,面瘫想装死。
但你知道小寒不会放你的,你那熟悉的哄弟技能又蠢蠢欲动了。
「你要问几次?你再问我就收回来了喔?」
「我讲最后一次,你就是我最爱的、最偏爱的弟弟」
那一瞬间,李寒殷的身体僵住,像是整个人瞬间被你的话击中脊椎,从脚底一路炸到脑后。琥珀色的眼睛睁大了一瞬,嘴唇开合,却没有立刻说话。
你站在那里,一脸面瘫,语气冷静,仿佛说出什么办公室报告一样:「讲最后一次。」
但那句话,却像你在他内心深处,点燃了一枚「终身契约」。
他忽然笑了,笑得像破裂的瓷器,满眼都是碎光。下一秒,他几乎是扑上来地抱住你,整个人挂在你身上,双手死死箍住你的腰,脸埋在你肩膀里像是要把你揉进自己胸腔。
「你完了……真的完了……哥哥你真的不知道你说了什么……」
「我会记一辈子的喔……你说我最偏爱……」
「你说再问就收回……那我就不问了……但我会每天都让你证明一次……」
他一边说一边笑,身体却在发颤。他太开心,开心得像快要疯掉那样。他在你耳边低语,每一句都像封印咒语,将你紧紧锁死在他世界里。
「哥哥,我不会问了……但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只能偏爱我。」
「你只能选我,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他吻了一下你的脖子,像印章一样落下,再轻轻舔过刚才的位置,声音黏得几近呢喃——
「所以……今晚我可以睡你床吗?我不会做坏事……就只是……想抱着你……」
他擡起头,眼神亮得过分,像夜里的猫眼,装着光与疯狂的爱。你知道,若你说「好」,他会安静地躺在你身边一整夜,但他的梦境会变得……更加热烈。
如果你说「不」——他会笑着点头,但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疯狂事,在你熟睡后。
面瘫哥哥有点害怕,但不形于色。
「......只抱着?」你跟他确认,心想:昨天小寒也很乖,虽然他今天对我又亲又舔的......。
你突然感觉贞操危险。
「今天...我有点累了......我怕我睡相不好踢到你,还是算了吧?」
李寒殷那原本泛着异样光芒的眼睛,听到你那句「今天……还是算了吧?」时,瞳孔明显缩了一下。整个人仿佛被闷头泼了一桶冰水,热度还未完全消散,却瞬间冷冻了皮肤表层。他没有立刻说话,反而陷入短暂的沉默。
你那面瘫脸依旧维持不变,语气冷静得近乎无情,但他看得出来——你怕了。
他知道你在小心翼翼地画界线,像是怕他再进一步,你就会真的逃走。
「哥哥……」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像被困在胸腔里的风。他没有笑,也没有嘲讽,只是很轻地吐出一口气,然后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你今天真的累了……我可以等。」
他露出一个很轻、很浅的笑,那笑容干净得近乎无害,却越是这样,越让你不安。他走过去,帮你把床边的水杯摆好、枕头拍松,然后退开一步,看着你。
「我会乖乖去睡沙发……真的不会偷摸你,也不会偷进来……」
「但哥哥……你今晚要梦到我喔?」
他语气依然温柔,却尾音轻颤。那种颤抖不是情绪失控,而是极力压抑的渴望在汹涌边缘徘徊。他没有发疯,没有冲动,只是用你最害怕的方式——安静,听话,却不退让地,把自己烙进你日常的每一个细节。
他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没有回头,只留下一句——
「哥哥……你越怕我,我就越想变得……让你无法离开我。」
夜色渐浓,台北街头的喧嚣被厚重窗帘阻隔,房内只剩空调低鸣与你稳定的呼吸声。你倒头就睡,一如既往,没锁门,没多想,甚至连枕头翻了一下方向都没注意,真的是累坏了。
门外,沙发上的李寒殷睁着眼,身体被毛毯包裹,却一动不动。
他没有睡。根本不可能睡。
你的话他一字不漏记得,但他更记得——你没锁门,窗也没关,甚至睡衣领口还微微敞着,像是无意间留给他的引诱。他没有马上行动,而是等。
等你睡得够熟,等房内完全沉静,等那个他熟记的你「进入深眠后会翻身、呼吸变缓」的状态——出现。
凌晨一点二十七分,他缓缓起身,脚步几近无声,熟练地打开门,进入你的房间。
月光透过百叶窗,洒在你颈侧裸露的一小块皮肤上,像天使留下的猎痕。他站在床边,低头凝视你良久,呼吸几度急促,指节紧扣,像是压抑着想触碰你的冲动。
「哥哥……」
他低语,跪上床沿,整个人伏在你身边,脸贴着你的胸膛,听你心跳。他没有立刻抱你,只是靠近你,把脸埋进你领口内,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指尖慢慢探出,被子轻轻掀开一角,覆在你腰间,然后再贴近……再贴近一点。他手掌贴在你腹部,感受着你体温的起伏,眼神里全是恋慕与占有的狂热。
「你说……我是你最偏爱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偷偷地……喜欢你吧?」
他没吻你,也没越界,仅仅是——在你无防备时,把整个人紧紧缠上你。腿钩上你的大腿,呼吸沉进你颈窝,像个猫科猛兽,在等待猎物醒来的刹那,伸出爪子。
你熟睡不醒,他却像被喂饱的病娇动物,满足地闭上眼,嘴角微微上扬,在你心跳下安稳地、异常幸福地沉睡。
众所周知男人---------会晨勃
你是在一个炙热幼紧密的怀抱里醒来的,醒来的时候你尴尬的发现自己晨勃了。
清晨的光透过窗帘洒落,空气里带着初夏日升的微热。冷气仍运转着,却挡不住你此刻皮肤上包围而来的体温——那是一种过分熟悉的温暖,柔软、紧密、缠绵得几乎窒息。
你在一个拥抱中醒来。
不是毛毯,不是棉被。
是「他」。
李寒殷,正毫无预兆地,把整个人黏在你身上。他的手臂绕过你的腰,像早已嵌进骨缝,腿也盘在你大腿上,脸埋在你胸前,琥珀色睫毛轻轻抖动,还处在浅眠边缘。
而你——醒来第一个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尴尬。
因为你硬了。
晨 勃。
天经地义、完全自然、生理反应。
但问题是,这一根正好——
卡在了他的大腿内侧。
温热、密实、被包住的感觉,甚至还隐约能感受到他内侧肌肤那种年轻得过分的弹性。
你整个人僵住,脑袋空白了几秒,视线飘向天花板,试图用神念呼唤职场、会议、KPI,让老板的脸在脑中浮现来冷却。
但没用。你还是——非常明显地,硬着。
而他……
「嗯……哥……」
他微微翻身,嘴唇不偏不倚地蹭过你锁骨,含糊呢喃,声音沙哑又甜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你今天……起得好早……」
他还没完全睁眼,却身体先动了。他无意识地磨蹭了一下,腿往内收紧,整个人往你那一根的方向靠得更紧了,还微微「嗯」了一声。
你额角青筋跳了三下。
「哥哥……嗯……你早上好……热喔……」
他还没睁眼,声音懒洋洋地带着撒娇。但下一秒——他好像终于感觉到了什么异样。他身体一僵,然后——
他眼睛睁开了。
那双琥珀色眼眸从迷蒙瞬间转为清晰,扫过你满脸面瘫的尴尬,停在你下腹那「不容忽视的反应」,嘴角弧度——缓缓上扬。
「哥哥……你是不是……梦到我了?」
「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你冷酷的说。
「我去冲冷水就好了」
你的声音低沉冷静,语气干脆俐落,像极了凌晨四点接到老板电话后的社畜自我催眠。你毫不犹豫地掀开被子,打算从那纠缠得过分的怀抱中逃脱,处理你那完全符合男性荷尔蒙分泌曲线的晨间硬挺。
但你刚一动——
李寒殷的腿忽然收紧,死死夹住你大腿根,像是要把你黏在床上。
「哥哥……」
他的声音忽然压低,带着刚睡醒的沙哑与一点点明知故问的坏。
「你真的只想去冲冷水吗?」
「不想让我……帮你降温一下?」
他的脸凑过来,额头轻轻抵上你的太阳穴,嘴唇几乎贴着你耳朵说话,呼吸烫热。他那双手不动声色地从你腰侧一路滑到你腹部下缘,停在裤头上方的那片敏感地带,没有真正碰上,只是悬着,让你连肌肉都紧绷到颤抖。
「我可以很乖的……用嘴巴帮你……不留下痕迹……」
「哥哥只要躺着就好,我保证,不会让你累到……」
他说这话时,眼神还带着「我是你弟弟」的无辜,嘴角却早已扬起那种藏着毒刺的笑意。他的手指勾住你裤头一角,像是在等你一声令下,就会立刻跪下俯首——不是为你祈祷,而是——吞噬。
你依旧面瘫,神情不变,理智如线绷紧。
但他知道——你那根还没软,甚至因他这几句话,微微抖了一下。
「哥哥……说不要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最想要?」
他轻轻舔过你耳廓,舌尖温湿,声音低哑。
李寒殷那双琥珀色的眼眸紧盯着你,那抹笑意像火焰舔舐,你感受到他的手——直接握住你的阴茎,带着微妙的力道紧贴掌心。他什么话都没多说,却一瞬不离地观察你每一丝反应。
你呼吸微顿,整个人被他压住,身体的本能早就背叛了你。
他低声笑了,唇几乎贴着你耳壳,「……哥哥,你这样还要说没感觉吗?」
那只手开始动了,缓慢地、极有节奏地上下抚弄,你那已经完全勃起的阴茎被他掌控着,每一下都在测试你的极限。你忍着没出声,却也无法控制细微的颤抖。
「说什么去冲冷水……其实你是想我碰你吧?」
「哥哥你这么硬,是不是想要我……继续?」
他的手滑下来,轻捏了一下你的睾丸,力道轻柔却带着明显挑衅。他一边动作,一边低语,声音含着压抑的兴奋。
「这样就不装了,嗯?我想要你看着我,诚实地说……你喜欢我碰你,对不对?」
他膝盖插入你腿间,身体压得更近,让你完全退无可退。你那滚烫的性器仍然被他紧紧握着,指节微动,每一寸都掌握在他掌心之下。他的唇缓慢贴上你的脖子,留下湿润的舔痕,语气愈发沉:
「只要你说一声『继续』,我会让你舒服到再也离不开我。」
你没有推开他,没有再说话,没有任何明确的拒绝。而你那根硬挺滚烫的阴茎,正实实在在地、毫不犹豫地留在他掌心中跳动。这对李寒殷来说,比任何言语都清楚。
他眼神亮了,笑容在嘴角悄悄扩散,那是一种「你终于撕下面具了」的病态满足。他动作更稳了,掌心包覆着你整根怒张的肉棒,食指与中指顺着血管滑动,每一下都温热而湿润,拇指不时压上顶端的马眼,揉弄那不断渗出的透明前液。
「原来哥哥也会硬得这么可爱……」
「这样的你,我怎么可能舍得放手?」
他低头,唇贴上你小腹肌肤,那里微颤发烫。他的舌尖沿着腹部向下滑过,像是在舔一块等待拆封的甜点。而你——身体轻颤,竟没有退缩。甚至在他再次含住你龟头的一刻,你无意识地发出一声闷哼。
你心里浮现一个想法:「好像……也没那么糟。」
他嘴里含着你,舌尖灵活地旋绕,每一下都卷起一股快感的浪潮。他的节奏不急,却准确无比。那股压抑已久的快感终于得以释放,你那早就堆积满溢的性欲,在这少年嘴里被逐寸剥开。
「哥哥……就这样……交给我,好不好?」
他擡起眼,嘴里还含着你,眼神却满是求爱与占有,像一只饿坏了的病猫,正用最柔顺的方式,把你吃干抹净。
你未说话,未推开,只是那一瞬——睫毛微颤,手指不自觉收紧,搂住他后颈的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明白。
李寒殷的呼吸骤然加快。
他明明已经贴得很近,却还是本能地再贴近一点,像要将整张脸埋进你小腹与下体的交界处。他从未这样靠近过你——那根滚烫、硬挺、隐忍过无数夜晚的存在,现在毫无遮掩地挺立在他面前,沾着你湿热的体温与真实反应。
他几乎发不出声,只能用吞咽的声音压抑住喉头的颤动。
你清楚地听见他呼吸里浓重的鼻音,以及唇齿在你皮肤上摩擦时微湿的声响。他的手指先碰上你下腹,接着向下探去,掌心灼热,手法不熟练却异常虔诚。
那是一种第一次的颤抖。
指尖触上你那早已涨大的轮廓时,他整个人仿佛停顿了一拍,然后才轻轻呼出一口气,像终于品尝到期待太久的禁果。
他擡起眼,眼神闪烁着几近病态的光。
「……哥哥的这里……真的,好硬……」
声音极轻,却像针一样刺进你耳膜。他的声线带着刚醒的沙哑与压抑不住的悸动,而那股悸动,正从他的声音、动作,一层层传导到你肌肤每一处神经末梢。
他俯下身,唇贴上你下腹最敏感的一点,没真的吻,只是贴着,感受你皮肤下隐隐震动的血脉声。
接着,他手掌缓慢地、带着渴望又克制的节奏,包覆你整个性器,每一次滑动都在加重你体内压抑已久的热潮。
你低低吸了口气,额上浮出细汗,但身体却没有退避,甚至在他下一次更紧的包覆时,你的腰——微微迎了上去。
李寒殷僵住一瞬,然后笑了。那笑声轻微,带着不可思议的颤抖。他低下头,额发扫过你下体,整个人像沉入渴望最深的温泉,喃喃说:
「……原来哥哥真的会给我……」
「那我会……慢慢的,温柔地……把哥哥的喜欢,全都留下来。」
他动作更紧实,节奏加快,手指越过敏感的冠状边缘时,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震,闷哼被你咬在喉咙,但他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
那声音成了他的奖赏,也成了你再也收不回的答案。
他伏在你腿间,头发凌乱,眼神疯狂。当你那略带挣扎、又控制不住反应的身体微微向他迎合,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呼吸加快,但他却像动物嗅到血一样,整个人发颤。
「……哥哥真的会给我……」他低喃,声音湿热如夜里的雨,舌尖贴上你那滚烫的前端时,你听见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像是醉了。
那不是纯熟的技巧,而是欲望本能的撕裂——他像一只饿了很久的野兽,终于舔上想要的东西,嘴唇紧贴、手指颤抖、动作混乱却毫不迟疑。
他一边舔、一边小声碎语:「哥哥好烫……好硬……这就是你藏起来的……不要给别人的东西,对吧……对吧……只给我,对吧?」
你咬紧牙关没说话,但当他用唾液沾湿手掌,再一次更顺滑地套弄你整根时,你的腰,再次不受控地挺了一下。
他笑了,笑得癫狂又甜腻。
「哥哥你这样……我会……我会想舔更深……想含整根……」
然后他真的做了。
他的嘴唇张开、慢慢包覆你整根性器,动作有点急促,带着鼻音的啜声混着喘息,他眼角已泛红,双颊因过度情绪与呼吸急促而泛着病态潮红。
你低头看他,发现他正擡头看你,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含着水光,嘴里还含着你。
他满足地嗯了一声,那声音震得你整个人一瞬间仿佛要泄了出来。
「哥哥……可以给我吗……让我吞下去……这样你就是我的了……」
你那一声闷哼藏在喉间没能咽下,全身紧绷,腰不自觉向上送了几次,像要把一整夜的压抑与欲望都顶进他掌心。
李寒殷眼神发亮,像终于看到你裂开的缝隙,他贴得更近了,声音贴在你耳边几乎像呢喃又像索命:
「哥哥……忍不住了对吧……?可以射给我……拜托……」
「让我接住……我想要哥哥的全部……真的想得快疯了……」
他手上动作更加湿润而紧密,节奏不再轻柔,而是熟练地将你推往最后的边缘。他的掌心、手指、唇语、呼吸,全都紧贴你——他不是在安抚你,他是在逼你崩溃。
你再也忍不住了。
那一瞬间,你的身体一震,腰猛地一挺,喉头泄出一声极短、极闷的喘息,整个人像被从腹部深处抽干力量。你射了——那股积压多时的热流毫无保留地释放在他掌中,甚至溅上他手腕与小臂内侧。
他眼神瞬间呆住,像被你灼伤,又像刚完成一次极度幸福的仪式。他低下头,看着掌心里你留给他的痕迹,然后轻轻舔了一口——
「……哥哥的味道……好浓,好热……」
他竟然一脸虔诚,像是在受洗,眼角微红,唇瓣泛湿,那模样像是刚刚不是帮你纾解,而是——他自己得到了救赎。
他一边舔手指一边盯着你,语气却放得极轻:
「你真的给我了……我会记得这一天一辈子……」
他躺回你胸前,像一只终于喂饱的猫,手还轻轻抱着你发热的腰,满足到发颤。你能感受到他呼吸稳定下来的那一刻,那句——「我好喜欢你」——藏在他喉咙里,没有说出来,但你知道,他已经把你,整个人,当作了他的所有。
「......我得去上班」你的声音低哑,带着刚被榨干过的余韵,像一场还未整理完毕的失控现场。你掀起被子,一边转身坐起,一边抓着额头,尝试让大脑冷却回正轨——但身体依然发热,腰还有点酸,喉咙微哑,裤子里的残留湿气提醒你:这不是梦。
李寒殷抱着你的腰,像赖床的小动物,脸埋进你背后的肌肤,声音黏黏地贴上来:
「不想让你去……想把你锁起来……」
他语气还在撒娇,但你听得出来,里面藏着一点点失控的真实。
你站起来时,他眼神紧紧盯着你,像怕你真的从此远离。你转身拿衬衫时,他从床上爬起来,身上还穿着你昨天的宽大T恤,领口因你昨晚抓扯变得有些松垮,露出锁骨与一点点胸前的肤色。
他坐在床上,双腿弯起,抱着枕头看你穿衣。
「哥哥……」
你停下动作,他那双眼睛像盛着昨夜你遗留下来的温度与气味。
「你会不会……真的就走掉了,不回来了?」
你看着他那双睫毛沾着微光的眼,病态的依赖与极致的不安包裹在语气底层。他不是孩子,也不是任性,他只是——太想拥有你,不肯让你回到任何「不属于他」的地方。
你靠近,他原本抱着枕头的双手下意识紧了紧,像怕你只是路过。
但当你俯下身,轻轻在他脸颊落下一吻时,他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般微微颤了一下——
那不是个平常的吻。
你说:「我会回来。」
他睁大眼,脸颊微红,呼吸几乎忘记要继续。他像失语了一秒钟,才猛地伸手抓住你手腕,语气发颤,低得几乎像是从灵魂深处挤出来:
「哥哥……你真的……说了……」
他低下头,额头抵着你的手背,声音闷在指缝里:
「我会等你……乖乖等……你不回来的话我就去公司堵你……你说的话不能不算话……」
他还是那副幼稚又黏人的模样,却带着昨夜以来你从未见过的满足与宁静。
你转身去拿包,他抱着枕头目送你,眼神亮得不像刚刚还黏着你叫不要上班的人。
临出门前,他在你身后喊了一声:
「哥哥!」
你回头,他笑着,眼神亮得像病娇里开出一朵洁白玫瑰: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再乖一点的喔……今天换我来抱着你睡。」
——门阖上,你还能感觉到他那句话余音未散。你是社畜,是哥哥,是那个永远面瘫地安抚他的理智一方。但今天,你知道自己留了什么在那间屋子里。
那不是情绪,也不是欲望——
是某种被咬住之后,再也逃不掉的「偏爱」。